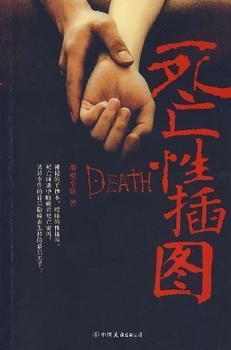死亡殿堂(瓶邪微黑花)-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一瞬间,我觉得秀秀的笑是那么刺眼,还不如哭来的更加自然一点。
“吴邪哥哥,对不起。如果你不肯原谅我,我可以现在就安排人送你回去。我只求你不要叫我霍小姐,我怕有一天,连我自己都会忘了世上有个人叫秀秀,而非霍家当家,就像奶奶一样。吴邪哥哥,帮我记住秀秀。”
秀秀,你都这么说了,叫我怎么不原谅你。算了,心软这毛病,治不好伤己,治好了伤人伤己,由得它去吧。
“不是说让我来帮忙吗?帮什么忙?”我摸了摸鼻子,掩饰刚才的尴尬。
秀秀讶异地睁大了眼睛,随即笑得眉眼弯弯:“吴邪哥哥,你真好,跟我来吧。”
我跟在秀秀身后,秀秀猛的一转身,我差点和她撞个满怀。
“吴邪哥哥,相信我,我永远不会伤害你的。”
我惊讶地看着她,她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怎么?不相信?我们可以拉勾。”秀秀伸出小指。
我被秀秀弄得有点无奈,说道:“那么大个人了,明天就要出嫁了,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
秀秀撇了撇嘴,收回了自己的小指。
忙活了半天,我终于可以回到酒店休息,小哥还没有回来,或者是回来又出去了。我忙累了,也没多想什么,直接倒头就睡。睡醒了,我发现床边坐了个人。
“小哥,你回来了。”
“嗯。”
就在这时,小哥把一块石头样的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揉了揉睡得不太清明的眼睛再仔细看手中的物件,那是···黑欧泊!鸽蛋大的黑欧泊!质地好的黑欧泊可是价比钻石啊!
“小哥,你今天出去就是在整这块黑欧泊?”
没有说话,应该是了。
晚上,我正打算就寝了,一通电话把我从被窝里撩了出来。
“喂,秀秀。”
那头没有应声,而且环境十分嘈杂。
过了好一会了,电话那头才传来声音:“我在红亭,你来接我吧,不许带哑巴张!”
“红亭?那是什么地方?”
“酒吧。”
“你在玩什么?”我气急败坏地问她。她知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
“···单身派对。”
我没让小哥陪我一块儿去,赶到红亭时,我看到秀秀缩在沙发里,旁边有几个女孩陪着,前面的桌子上摆满了酒瓶。她看到了我,朝我摆手。
秀秀喝了很多,双眼都迷离了。我俯下身扶她,这时,她伸手搂着我的脖子说:“吴邪哥哥,你带我私奔吧···”
我惊得手一松,秀秀直接跌回了沙发里。
秀秀撑着沙发自己站起来,似醉非醉地说:“开玩笑的,别紧张啦!”
秀秀,不要随便开玩笑,人吓人才能吓死人。
我想要再去扶她,她却一手把我推开,一个人步履蹒跚地走到了门口。
出租车上,她继续把自己团成了一团。看着她的样子,我觉得特可怜,就像是被抛弃的猫,只好把自己缩成一团来寻求温暖。我想,她一定不喜欢佟学。
“秀秀,觉得委屈的话就哭出来。”我不知道她到底醉没醉,也不知道我说的话她能不能听清。
“我不委屈,奶奶说过,这辈子如果不能嫁你最爱的人,那就嫁对你最有利的人。我不委屈。”秀秀从自己的臂弯里探出个脑袋说道,“吴邪哥哥,你一定要幸福哦!一定要比秀秀幸福哦!还有小花哥哥···”
我看向秀秀时,发现她早已泪流满面。
我把秀秀送回了霍家,出来时,是一种五味杂陈的心情。
下面是秀秀与三叔的通话内容,用第三人称写。正文用第一人称写,太多东西都没办法交代清楚,以后我还是多尝试上帝视角吧。
“请问哪位?”潘子接起他家三爷家的座机问道。因为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吴三省都不会亲自去接。
“三爷在家吗?我是霍秀秀。”
潘子迅速地在纸上写下了个“霍”字,询问吴三省这电话接还是不接?
“哦,是霍小姐啊~~”潘子一边说,一边望着自家三爷,等待他点头或摇头。
吴三省盘算了一下,正好趁这机会告诉霍秀秀,她那婚礼,我就不去了,现在霍家正处风口浪尖上,他可不想凑上去被海浪拍在沙滩上,所以这电话得接。
“我这就把电话给三爷。”
吴三省接过电话,那头传来秀秀的声音:“三叔,我是秀秀,您看我还像以前一样叫您三叔成吗?”
“秀秀啊。你后天就要结婚了是不?你看三叔老胳膊老腿的,跑不动了,你那婚礼,三叔就不去凑热闹了。”
“三叔,老胳膊老腿的还到处下地,您那理由也忒不靠谱了,您也不想个正经点的来糊弄我们小辈。告诉您吧,我的婚礼,您是不想来也得来了,而且还非得表示一下乐意帮助我霍家不可。”
吴三省一听,自己活了那么大把年纪,还能被你一小丫头要挟?他倒要看看这小丫头耍的是什么花头!
“此话怎讲?”
“三叔,吴邪哥哥在我这儿,和小哥一起哦,他们就在我给安排的房间里。您说,我要是下点药,成全了他们的好事,再用针孔摄像机拍下来给吴大伯寄去,然后告诉吴大伯,他儿子和小哥是您老人家给做的大媒,这故事会不会特别的精彩?”
吴三省一想到他那大哥二哥,瞬间脸就白了。
“三叔,我的婚礼您倒是来不来?我们霍家您倒是帮不帮?”
最后,吴三省咬牙切齿说道:“好。”
吴三省,K。O。
第26章 第二十一章 变
秀秀的婚礼,除了隆重二字,我想不出其他什么词来形容,好像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彰显佟家的财力,这里不说也罢。
第二天我就和小哥回杭州了,北京这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待下去。我不知道这繁华都市里的灯红酒绿下是多少人的寂寞哀伤,这锦绣皇都中的车水马龙间是多少人的彷徨无奈,多少人像秀秀一样,为了家族,为了荣光,要拿自己的幸福献祭。有时候我想,要是秀秀自私一点,软弱一点,那么她会不会笑得更真实一点?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假设不会成立。
回到杭州后的这几天,小哥的行为很怪异,跟他说话,他老心不在焉,有时要说第二遍他才反应过来,还时不时地往外跑,就好像在筹谋着什么事。其实他这怪异的行为在北京时就有了,只是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而现在,这种情况让我很害怕,害怕他突然间就消失了。
“小哥,你最近怎么老是往外赶?”我问他。
“有一些事要处理。”
说了等于没说的回答。我知道我休想从他嘴里问出些什么来了。
我有点累了。
真的。
小哥他那么容易就进入了我的世界,而我历经千辛万苦却连他的世界的边缘都触碰不到。
我知道他叫张起灵,我知道他有一身好功夫,我知道他的老闷宝血是万能的,我知道他时不时会失忆,我知道他总能救我于危难之中。
然后呢?
然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很感激他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可是我要的不是一个保镖,我要的是一个可以相依相伴的人,我们可以站在对等的位置上,相互扶持。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我们就在同一屋檐下,我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能怀着忐忑的心情去猜他到底在想什么,猜到最后,是一次又一次的问自己,小哥真的在乎过你吗?可悲的是,我连给自己一个肯定回答的勇气都没有。
这几天,我觉得我过得很悲惨,吃饭饭不香,喝茶茶无味,连王盟都有所察觉,对我说:“老板,你最近为何如此怨念深重?我们铺子本来客人就少,被你漂浮于空气中的怨念又给吓走了一半,生意惨淡的事真不能怨我。”就只有他,就跟个没事人似的,对我不闻不问,自干自的。
终于在一个晚上,就着床头蓝色的昏暗灯光,我对他说:“小哥,哪天你要离开了,记得提前跟我说一声。”
他转身望着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一直追着你不放的是我,先表白的也是我,我怕哪天你厌倦了我,想要离开了,不要一声不响就消失,先告诉我一声,也好让我有个准备。”
小哥啊,原来我爱你爱得那么卑微。不要一声不响就消失,先告诉我一声,也好让我有个准备。我对你的要求就只有这些。
小哥握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按在他左胸口上,有力的心跳从掌心传递过来。“感觉到了吗?现在你是它跳动的意义。”他说,“别想太多,睡吧。”
你是它跳动的意义?刚才我是听到了这样一句话?我没有幻听?
“小哥,你刚才说了什么?再说一遍。”我相信在这暗夜里,我看向小哥的满含兴奋与期待的近视眼绝对比灯光还要明亮!
“睡觉。”
“不是这句,前面一句。”
“别想太多。”
“也不是这句,还要前面一句。”
“忘了。”
怎么可以忘了···
就这样,我感觉着小哥的心跳,一夜无梦。
于是,我就忽略了他还没有回答我会不会消失,会不会告诉我···
第二天醒来,身边的位置早已凉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早走,而我傻傻地以为着他会在中午,下午,或是晚上的某个时间突然出现,就像往常一样。可惜没有,他没有回来。饭菜被来回热了两遍,然后倒掉。
我等了三天,三天里,王盟的玩笑少了,叹息声多了。小哥,你才出去几天,就把王盟一屌丝2B青年变成了忧郁青年,一个人养成个习惯还要十天半个月的,你改变一个人的属性都只要三天。
三天了,我不想承认,但又必须要承认了。小哥终究是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话。我被抛弃了。
前一秒你还说我是你心跳的意义,后一秒你就离我而去,这算什么?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手拿糖葫芦的小孩,为了手里好不容易得到的糖葫芦而欢天喜地,不曾想,那么快它就落入泥潭之中,于孩子而言,这种反差带来的失落是可以天塌地陷的。我若是个小孩,还可以痛哭一场,可是我不是,我能做什么?
王盟整天摆着张苦瓜脸,弄得我现在看到瓜就想吐,看到绿色也想吐。我不知道那三天里我到底吃了多少,反正王盟说,那三天是他进店以来最铺张浪费的三天,他从来没有见过垃圾篓里多出过那么多饭和菜。
铺张浪费可不是个好习惯,以后该吃多少还是吃多少吧。想着之前隐隐约约那绝食之势,我不禁觉得有点好笑,又不是小女孩,这一哭二闹三上吊般的架势是要做给谁看呀!还吓着了我们王萌萌同学。我也想通了,小哥闹失踪也不是第一次,失踪去找就是了,就像回归从前,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是这么想着,心里还是难免有些酸酸的。有些伤,不是说治愈就能治愈的。
王盟这些天又要照看铺子又要照顾我,倒也难为他了,是该好好犒赏犒赏他。
我悄悄走到他身后,只见他左手托着腮帮子,一声“唉~”,换右手托着腮帮子,又是一声“唉~”。
“王盟,你是不是在考虑把这铺子变成酱瓜铺,酱苦瓜。”
王盟被我突然的出声吓了一跳:“老老老老板,你怎么来了?”
“今天晚上请你下馆子。”
王盟继续作惊吓状,转瞬又用看外星人的目光看着我:“老板,你是病情转好了还是更糟了?”他看了我一圈,突然带了哭腔道:“完了完了,我看是更糟了,老板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
难道我在王盟眼里就是一个一毛不拔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