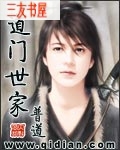百败小赢家-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哟,怎么了?公子爷?”陈妈妈显然吓了一跳。
“腿……腿麻了……”苦着个脸,小豹子只得实话实说。
“来,陈妈妈背你好了。”
“不,不,我……我还可以走……”
让这种人背,小豹子宁愿骑上一头母牛的背。
躲不过的事情只有泰然处之。
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
这是小豹子的格言。所以回到房里后,他开始老实不客气的大吃大喝,说实在的,折腾了一下午他早已饿得两眼发花,只不过刚才心里太紧张没去注意。
现在想开了他就啥也不管,夏荷一旁殷勤的又挟菜、又添酒,忙得不亦乐乎。
如果她要知道这小子打谱是白吃白喝外带白玩的话,恐怕她会一根根拆了小豹子的骨头。
“呃”的一声,小豹子打了一个饱隔,接过来夏荷递过来的热手巾擦了把脸后,他摸了摸鼓涨的肚皮。
“赵公子,您……您吃饱了?”
“嗯。”
“您……您喝足了。”
“嗯。”
“是不是……现在……”
“你到底要说什么就快说,呃,本公子……本公子已快醉了……”小豹子一张稚气的脸上已因酒意而红。
“这……这饱暖思……让夏荷扶您到床上……”
敢情姨子还真现实,夏荷巴不得早办完事早拿银子。其实她本不急,然而她己怀疑,因为打进门到现在这看似有钱的公子到现在连一分赏钱也没拿出来过。
“上床?呃,好,好上床,啊?不,不,慢点,慢点,让我想……我怎么会到这来的?我来这要干什么?”小豹子酒意已上头,思路开始紊乱。
“赵公子,您……您真爱说笑。”已经觉得有些不对,夏荷勉强一笑说。
“不,我……我好像是来找人的。对,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你没弄错吧?”夏荷脸己变。
“对,我是来找糊……糊涂蛋……找他……找他去……去救……去救我的……星……星……”
一个小孩酒量有多大?
整整一小缸陈年女儿红下了小豹子的肚,他当然不只舌头已大,现在,就是现在他己像滩烂泥一般瘫在床上人事不醒。
贾裕祖的手轻轻托起小星星的头。
他那张阴鸷的脸上己泛起一种兴奋之色。
“好,好,果然是颗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哈哈……”
小星星从小豹子被丢出门外后就一直两眼盯着门口,直到“辣手”贾裕祖的手摸向自己的脸,她才机伶一颤,像碰到鬼一样的朝后直退,惊慌失色的双唇打颤。
“小星星,你最好弄清楚,你现在已是我的人了。”
“不,不,你胡说……”小星星急得冷汗直流。
“胡说?”贾裕祖阴狠的说:“我怎么胡说了?你莫忘了你巳让那头‘豹子’输给了我,是你自己太信他的赌技,你要明白,也是你自己想赢我怀中的‘星星’。”
“我……我再也不相信他了……我……我永远也不相信他了……”
“要不要我告诉你实话?”贾裕祖笑得十分得意。
“实话?什么实话?”小星星被他那古怪的神态引发了心中的好奇。
“就是他怎么输的呀!”
“你……你作弊,你作弊是不?我知道你一定作弊才赢了小豹……”小星星已然想到。
冷哼一声,“辣手”贾裕祖说:“我开场子开了一辈子就从没碰到过这种要把人逼上绝路的‘来人’,他不想让我混,我还要对他客气?你说对了,本来是他赢的,不过也只怪他太嫩了才会栽了跟斗,我这只是给他一个教训,要他知道以后做人厚道点,否则我大可以剁了他的双手,割下他那双可以听出点子的耳朵。”
小星星的眼睛睁得好大、好大。
她怎么也想不到刚才那场赌局小豹子既然是赢家,又怎么会变成了输家?
根本忘了自身的安危,她现在只希望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意的拿起桌上的宝盒,贾裕祖说:“现在仍是二个么点,一个两点对不?”
小星星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点了点头。
“现在我盖上盖子。”贾裕祖轻轻地盖好盖子:“你是知道的,我从进门到最后始终都没碰过这宝盒对不?”
小星星又点了点头,显然她要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把人输给了对方。
“你还记得不?我进门不久后曾经大笑过?”
笑?难道笑能笑出点子?
小星星沉思了一会,又点点头。
贾裕祖又“哈哈”笑了两声,仍然是笑声震耳、震瓦,更震得人心一跳。
然后他掀起了宝盒;小星星傻了。
因为宝盒里的散子点数已变,成了一个么点,两个两点。
“你……这……这是怎么回事?”小星星当然明白笑声有鬼。
“我这笑有个名称叫‘震天吼’,既然能震天,宝盒里的散子当然会有可能被我的笑声震得翻介面喽。只可惜那头‘豹子’耳朵再灵,被我的笑声一震根本听不出宝盒里的散子已经翻了个面。”
小星星明白了,然而也迟了。
许多事情迟了就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有时候迟了的代价包括了个人的生命,女人的清白。
小星星清纯得像颗天际最亮、最耀人眼的星星。
她虽然只是个孩子,但是碰到了贾裕祖这种“辣手催花”的人,她无异成了头绵羊,一头连一丝反抗余力都没有的绵羊。
她被安置在一间舒适的房间,她全身除了眼睛会动外就像一座雕像般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辣手”贾裕祖淫笑的一步步靠近,根本无视小星星眼中的惊恐,脸上的泪痕。
“乖,小宝贝,不要怕……不要怕……”
蓦然——
贾裕祖猛地退后数步,他直博博地瞪视着小星星颈项滑出的一块玉佩。然后,他开始流汗,一种发自内心的冷汗。
“你……你是‘四疯堂’的人?”
不错,小星星那块玉佩正面三个浮雕“四疯堂”不但醒目而且刺眼。
任何人都知道“四疯堂”在这淮中地区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势力。
任何人也都知道,够资格挂上“四疯堂”玉佩的人除了大当家的亲人之外没人有那个胆子。
糊涂蛋一脚高,一脚底,踩着有些不稳的脚步来到“对对胡”赌馆。
他那猥琐的脸上有种意犹未尽的满足。黄板牙的嘴里更哼着“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然后他的脸就真的“破碎”了。
因为同样的大门,同样的招牌,却不再是同样的对联,同样的字。
“对对胡”改成了“同安堂”。
两旁的对联却成了
私人住宅,闲人莫入。
内有恶犬,访客注意。
退后数步,他的六分酒意却全惊成了一身冷汗。
用手来回揉着眼睛,他嗄着嗓子自语:“这……这是怎么回事?妈的,莫非,莫非我真乐晕了头,跑错了门?”
左瞧瞧,右瞧瞧,他不再犹豫立刻上前敲门,因为他肯定自己并没跑错门,毕竟他记得很清楚“对对胡”赌馆的左右隔罐正是一间草药店,一间打铁铺。
“开门,开门,妈个巴子你们再不开门,老子一把火烧了这间鸟宅——”
敲了许久,隔壁的草药店老头靠近了他的身边问:“老乡,你找谁呀——”
“找——他奶奶的我是来赌博的——”
“噢,老乡,这间赌馆已经关门啦——”
“关门?什……什么意思?这间赌馆就和差馆一样,除非房子烧了怎么可能关门?”
“这你就不知道啦,就在前半个时辰,这间房子已经卖给了前街的张大户,你没瞧见,人家连招牌都换了。”
一个旱地拔葱,糊涂蛋翻进了院子,飞也似的旋进了大厅,触目所及,他差些瘫在当场。
一张大白纸贴在墙上。
字达吴必发护衙:
欲救星星,黄金万两,
三日之后,苦心庵见。
辣手贾裕祖百拜
惨了,惨了。
糊涂蛋出了大门后嘴里一直念叨着这两个宇。“小豹子、小祖宗,你……你们到底在哪?”
眼见天已黑,街上的商家全掌上灯,糊涂蛋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在街上乱转,更不时的逢人就问。
“请……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星星?”
“请……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豹子?”
心乱如麻的人问出来的话当然荒唐得离谱。
“星星!妈的,你神经病呀,你不会抬头看看,满天都是星星。”
“豹子?你以为这是动物园?”
碰上了这么荒唐的问话人,也无怪乎每一个人全拿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
“豹子,你害死我了,你叫我上当带着你们来‘莲花集’,现在可好,一个失踪,一个被掳,你……你叫我怎么回去覆命?”
急得想上吊的糊涂蛋望着人来人往的路人,一屁股坐在路边,苦恼得自言自语。
没找着那头要命的豹子,没问清星星如何被掳,他怎敢独自一人回“四疯堂”总舵?
因为他知道就算他回去禀完了事情发生的原由后,他的脑袋就再也不会多停留一会在他的脖子上。
事情也真凑巧,本来糊涂蛋出了“怡红院”的门应该可以发现“尼克森”。
然而只怪他贪走近路,偏偏放着前门不走,要走后门,他要知道的话,打死他恐怕这一辈子也再不敢走后门了。
“星星、星星。”
“我打得你满天金星——”
老鸨一把揪起几自说着醉话的小豹子,劈头盖脸赏了几个耳聪子后说:“小王八羔子,你给我醒醒,醒醒啊,你这个白吃、白玩的混蛋——”
她不得不气,也不得不恼,因为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半大孩子竟然有种身上一文钱也没有来逛窑子。
昏睡中两颊火辣辣的烧痛,小豹子张开惺松的醉眼,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呢,又是两记清脆的耳光,接着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
机伶一颤后,醒了,却也凉了。
“说,你是谁家的孩子?好哇,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老娘这可是没钱能来得的地方?”
混身湿淋淋的坐在地上,小豹子望着叉着腰,张着血盆大口的老鸨,心里已然明白“东窗事发”。
“我……是你拉我进来的……”捂着嘴,苦着脸,小豹子酒意全消。
“我拉你进来?小兔崽子,老娘怎么知道你荷包里连一个蹦子也没?我更没拿绳子拴着你进来啊——啊——啊——”
后三声“啊”一声比一声大,震得小豹子耳朵都快聋了。
他自小至大几曾有人敢用这种态度对他说话?
他又何曾挂过这种耳光?
一种作弄人的念头陡然生起,小豹子古怪一笑后说:“陈妈妈,你……你嘴里有三颗蛀牙……”
气得差些吐血,老鸨没想到这个孩子,这种时候,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你……你不要叫我陈妈妈……来人呀,给我把这小鬼吊起来……”
“慢点,慢点,我说陈婆婆、陈奶奶、陈太君,你干嘛要吊起我来?”
愈是人老珠黄的女人,愈是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称呼,这位陈妈妈巴不得别人叫她陈阿姨、陈姐姐。
现在入耳听到小豹子又是陈婆婆、陈奶奶的乱喊一气,早已气得差点闭过气,一件食指她吼道:“小兔崽子,你白吃白喝难道不该——哎唷——”
小豹子狠狠张开口咬住那伸在面前的指头,只见那老鸨眼泪鼻涕俱下,再也说不出话来。
“你……你们都是死人呀,还不赶快给老娘把这小王八羔子捆起来——”老鸨强缩回手指后,跳着脚,用另一只手捏住鲜血淋漓的手指,朝着门口两名大汉暴吼。
大汉固然吓人,可是要两名大汉去抓滑溜得像条泥锹的“豹子”,那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
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