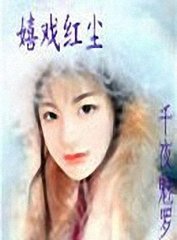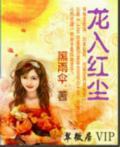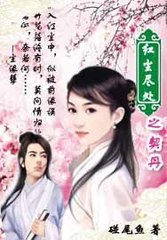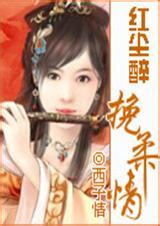红尘静思-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由台南补习班敬送往返飞机票,早上呼呼飞往,晚上呼呼飞返,机场有人恭接,休息有高级旅馆,虽拉阿伯王子下东洋,也不过如此,好不羡煞人也。
但各位读者老爷千万不要认为这也不错呀,补习班真是尊师重道。事实上补习班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机构,在这个现代化商业机构之中,财神高高在上,既没有“师”强调人要以行去体验道的存在。主张以“用”见人之才能。反,也没有“道”,所以也就根本无法去“尊”,更无法去“重”。补习班里只有“推销员”和“主顾”,推销员是教习,主顾是学生。也可以说,补习班就是马戏团,教习就是小丑,学生就是观众。你能招待观众,你就是大牌红星第一等角色,不要说坐飞机,就是坐火箭,老板也千肯万肯。可是一旦你黔驴技穷,不能叫座,或年老色衰,门前冷落,彼时也,别说坐飞机,你就是甘愿坐钉子,老板也没钱买。
半年之前,一个回国不久,在某大学堂教数学的打狗脱,前来拜访,他深知柏老神通广大,拜托介绍教补习班。他是一个老实人,愁眉苦脸曰:“老头,你看我,靠大学堂的薪水,捉襟见肘。”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就帮了他一个忙,结果不到两个星期,面无人色地被赶出大门。呜呼,补习班的教习,跟一般学堂的教习不同,学问大不值一个屁,主要的必须能招蜂引蝶。学生跟教习之间,既没有师生名分,更没有师生感情。普通情形之下,银货两讫,交易而退,谁也不欠谁的。盖学生老爷没考上联考,掏出银子,来收买两套本领,准备明年再士,如果教习不能给他两套结结实实的考试功夫,学生们总不能让银子泡汤,当然拍拍屁股就走,去别的店铺打员有没有更好的货色。嗟夫,学生就是饭碗,饭碗生脚,教习能不生脚乎哉。
补习班老板,把教习当作摇钱树——对不起,越比喻越不像话,这当然不是说你阁下,请别多心。而只是,谁能为他摇钱,谁就是活宝,恶补老板抢着重钱礼聘,活宝一咳嗽,老板就掏阿斯匹林。如果摇不出钱来,就是爱因斯坦先生也不行。两节课下来,一看你讲的不见得抓住联考题目,学生立刻散了一半(没全部散掉已够面子啦),老板的脸色就像刚挨了破鞋底,如果再不知趣,第三堂仍敢走进教室,那恐怕真是世界上第一流胆大包天的冒险家。
补习班里,一切都是买卖,而且是无情的买卖,学生跟教习之间冷若冰霜,老板跟教习之间也冷若冰霜功之学”,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提倡“王霸并用,义利双行”。,而教习跟教习之间,同样冷若冰霜。柏老曾参观过台北最大的补习班之一,看到下课时的奇景,不禁吓了一跳。诸教习像沙丁鱼一样地挤在休息室,乌黑一片,却鸦雀无声,大家面目痴呆,筋疲力尽,互相间不交一语,不但谁也不知道谁姓啥,简直是谁也不知道谁是男是女。盖正式学堂上课,教习可慢慢地讲,扯扯闲话,发表发表属于自己的见解,训训学生出口自己的闷气,而补习班却是严阵以待,教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真刀真枪,一有冷场,就要卷铺盖,话题稍离考题,也得卷铺盖。严格说来,挣那份银子可真不容易,那不能称这为教书,只能称之为拼命。下得课来,自然奄奄一息。
有些恶补大王一星期能教五十六小时的课,不分昼夜,埋头苦讲,连星期天都不休息,目的不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是奋不顾身地赚钱。于是,台湾的教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恶补教习,小焉者生活宽裕,悠哉悠哉,大焉者除了没有私生活,没有人生的情趣外,其他应有尽有,汽车焉,洋房焉,有的甚至跟恶补老板比美,此乃第一等人物,使人起敬起畏。另外一类就不必提啦,只靠固定薪津的正规教习,面有菜色,迂不中及。
——其实当教习的,还有两条大路发展:一是搞上一个有钱或有权的腿抱之,弄个顾问、委员、董事、监事之类的名堂,一旦奉命,立即提笔上阵,搬出学术理论来支持大亨怎么搞都是正当的。另一个钻个官做做,“学而优则仕”,中外如此,谁也没啥可说。
问题是,教习老爷岂真愿当恶补大王哉,乃不得已也。现在的待遇,初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六七千元。高级中学堂的教习“非命”观点,强调“强力”、“功利”,提出“取实予名”、,每月大约八九千元。大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一万余元。我们说“大约”,因为教习每月到底多少钱,谁也不知道,教习自己也不知道,恐怕请主计会计的朋友张口,也一言难尽,盖数目无几,却名目繁多。倒转过来说,虽然名目繁多,却数目无几。生在笑贫不笑娼的工商社会,五口之家,真得有点挺劲。要想进一步的温饱——台湾亚热带气候,夏天长而且热,应该改为要想进一步的凉饱,如买个电风扇,或雄心万丈,买个二手货的冷气机之类,既然没有别的妙法,只好乞灵于恶补矣。
学生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是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也是使学生老爷考上学堂——学生老爷必须能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才有钱可拿。补习班老板像月下老人,把双方撮合在一起,两情相愿,各取所需。跟美容院一样,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再大的力量都无法把他们拆散,更阻挡不住它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借书不还,天打雷劈
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从它的国民阅读水准上,可以判断出来。你阁下如果不幸落到吃人部落的朋友们之手,战栗四顾,恐怕看到的全是悬挂高竿的头皮,绝不会看到一本书。假设你竟然看到一本书,请来个电话,我就输你一块钱。中国虽是文明古国,最近并且面不改色兼气不发喘地自封为文化大国,当然比新几内亚吃人部落要高三级,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把“书香世家”作为最优秀的家庭。柏杨先生说你是“书香世家”,你一定龙心大悦;柏杨先生说你是“小偷世家”,恐怕有揍可挨的。盖“书香”也者,在古时代表现实的权或潜在的权势,在现时则代表高贵气质。可是,套一句有学问的话:“自欧风东渐”,书香随书橱而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酒香四溢的洋大人的酒柜。
柏杨先生去拜访朋友(几乎每一次都是借钱),进得客厅,迎面而立的准是一个酒柜。客气一点的,酒柜则放在左右两厢。上面摆着写满了英文的“喂死剂”、“白烂弟”、“拿破轮”,把人看得如醉如痴。好容易屁股坐定,左张右望,虽然没有看到悬挂高竿的头皮,却也没有看到一本书。——不但没有一本书,有些家庭,简直连一份报也没有,谈起来太空人登陆月球的消息,全家都用一种嘲笑的眼光看着我,意思是说,借钱就借钱吧,撒这种谎干啥。
不看报还可称为“古之人也”,一切知识来自道听途说。不看书则比“古之人也”要更进一步,成了“吃人部落之人也”。进入这种人家,不见书橱,只见酒柜,没有书香,只有酒香。于是乎“书香世家”,变为“酒香世家”。
日本吸收外国文化,吸收的是精华。——注意一件事情,当八世纪他们“大化革新”,全接受中国文化时,事无巨细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照单全收,却扬弃了中国人最自豪的科举制度。这真是绝顶聪明,使他们免去了由于科举制度而产生出来的“官场”浩劫。中国吸收外国文化,吸收的只是洋大人身上的汗珠,用舌头舐那么一舐,就心花怒放,傲视群伦。酒柜大兴,不过现象之一。柏杨先生想当年阔的时候,客厅之中,就也有酒柜在焉,因为我老人家是不吃酒的,所以买了些洋文招贴的空酒瓶,里面灌上洗澡水,俨然一个伟大的西崽,来访客人,无不肃然起敬。偶尔有老朋友,硬要来一盅,我就请他来一盅,结果拉了肚子,病不瞑目(没有灌上尿,正是我老人家忠厚之处,读者老爷不可不知)。
这问题就出在眼光太短上,保看见了洋大人的酒柜,没有看见洋大人固是家家有书橱的也。大家努力崇洋,却只崇了一半,不知道我们为啥连日本朋友都不如。大概物极必反,最近酒柜有开始撤退的迹象,若干家庭的客厅,或有书橱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还有蓬勃的生机。不过有些摆的是美国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有些摆的是连断句都没有的二十五史,虽然从没有人翻阅,但用以炫耀主人学问庞大,已经足够。据报上说,竟有人在巨著中藏着“花雕”,酒劲发时,就展卷过瘾。——这干法属于左道旁门,不在讨论之列。
书橱所以迄今仍不能代替酒柜,或是只摆些样品似的大部头,原因固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出在借书上。有些恶客在朋友家发现一本好书,顿时暗起杀机,雀跃曰:“哎呀,老哥,借给俺瞧瞧!”一场悲剧于焉上场。盖自从盘古立天地,借酒的少,借书的多。借酒的从没有听说不还酒的,借一瓶“喂死剂”,准还一瓶“喂死剂”。借书则属于另一种伟大的景观,借一本《红楼梦》,可能还一本《红楼梦》,但是借一本古本《金瓶梅》,恐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加果借的是绝版珍本,该恶客可能举家潜逃,你就是弄个盖氏探测器,也探测不到影踪。夫珠宝失踪,或被借、或被俘,没有下文,还可告到衙门。而仅只一本书,如果劳师动众,恐怕同情的不是书主,而是恶客。河南省有句谚语曰:“偷书不算贼,捉住打锤。”此锤非铁锤头,乃拳头也。偷书属于雅贼,打一锤已经该诅咒啦,至于借而不还,理就比天都大——你摆着还不是摆着,俺拿来进德修业,以便救国救民,你不送慰劳金已够差劲啦,还有脸讨呀。
然而,一个人省吃俭用,好容易买了几本视同性命的巨著,却被列强瓜分,实在痛彻心肺。尤其雅贼也者波温(BordenParkerBowne,1847—1910)美国哲学家,人,真正借去拜读,倒还罢了,大多数都是往墙角一仍。据柏杨先生统计,借书归还的比率,不到十分之一,其他的不是有心于没,就是不知道弄到他妈的啥地方去啦。当其借书时也,如果拒绝,八十年交情从此一笔勾销,不得已借给他,再向他索取,不但索不到书,八址年交情也同样一笔勾销,而且还开骂曰:“几本破书,也不是银子,三番五次,要个没完,我早忘记塞到哪里去啦。哪一天我整理整理字纸篓,找到后摔到他脸上,老子也不是买不起。”书主被糟蹋到这种程度,怎能不潸然泪下欤。看起来书橱之代替酒柜,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候。
杜暹先生藏书万卷,每卷后都亲题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卖及借人为不孝。”在唐王朝那个时代,不孝是要杀头的。用杀头以阻止出借,是为磨刀阻吓法。吾友郭衣洞先生,在他的藏书上印有文曰:“笺笺稿费,买书自娱,且以之维生。辱蒙借阅,务清早日赐还,实万分感谢。”大概发现要想不借,比登天还难,只有婉转陈词,以求打动恶客芳心,是为摇尾乞怜法。
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是对牛弹琴。冒着杀头的危险而仍把书借人,可见恶客泰山压顶,超过杀头。既决心不还矣,靠几句求情的话,又岂能动他的铁石心肠乎哉。有一次我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