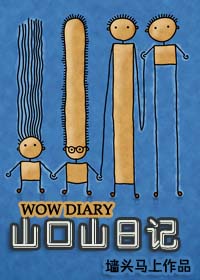偷情日记-第1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看火候差不多了,只身走到屋外,指着赵德全的鼻子骂道:“赵德全,你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找死是不?”
赵德全轻蔑地看着我,哼着鼻子说:“郁镇长,我可不是针对你来闹事。我老鹰嘴,老少几百口人,你们迁政府拿去了我们几百亩地,每家给个户口就算了。这次你们又搞我们一百亩,这一百亩可不是简单的地方,都是村里最好的水田,全村人一年的吃喝,全指靠它。现在你们一搞,你说我们怎么活?”
“草里还能饿死蛇?”我冷笑着说:“你这个样子,就是没出息的,你来,我告诉你。”
我朝他招招手,让他过来。他迟疑地看了看四周,不相信地说:“郁镇长,你没有叫郝所长又来抓我吧?”我笑笑说:“你怕抓,还来闹事,吃了豹子胆嘛。”
赵德全警惕地拿眼四处瞧,没见着郝强,才放心地假笑着挨过来,跟我保持半米宽的距离,直着脖子说:“你说,看你今日怎么忽悠我。”我依旧微笑着说:“赵德全,你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什么时候不把你们放在心上了?你听不听?听就老实过来,不听就给老子滚远点,你不滚,你看那是谁?”我指着站在三楼顶上的郝强,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别以为老子没防着你来这一手。”
赵德全抬头一眼看到郝强,作势就想跑。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在他耳边轻声说:“你们拿了农转非户口的人,难道不想都有个工作?”
赵德全一怔,狐疑地看着我:“你说的都是真的?”
“打包票。”我轻轻拍了一下胸脯子:“快给我滚,坏了好事,你就是跑到阎王老子哪里,也得拉你回来大卸八块,知道了?”
赵德全使劲地点头,转身一溜烟走了。走到盘小芹的超市门口,我看到从树底下钻出一帮老头老太,跟在他的屁股后面,逶逶迤迤地走。
这家伙原来还藏了一手!他是准备见势不妙就开溜的人,接下来就是一帮打也打不得,骂又骂不得的老头老太出场。
支走了赵德全,我返身回到会场,对关书记汇报说:“对不起,关书记,一点小事,处理好了。”
关书记赞许地点头,示意我继续主持签约仪式。
当郭伟从钱有余的手里接过合同书的时候,我如释重负般舒出一口气。这一场签约仪式,把我与郭伟的能力立判高下,一个镇委书记,在我这个镇长的面前,败得一塌糊涂。
等到送走了全部领导,我和郭伟长舒口气,跌坐在会场的椅子上,半天不想开口说话。
尘埃已落定,有了矿泉水厂,迁址政府是水到渠成。我想起黄微微还在我的小屋里,心里一阵欢喜,恨不得长双翅膀,立刻飞到她的身边去。
我要告诉她,这次我要跟她回衡岳市,一来把车送给小姨,二来我要去看看何家潇,自从他回去后在没给我电话,我感觉不正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娘了,我要回家!
220、承欢
省里传来消息,指示新政府工地不得开发,要等省里再次勘测发掘。
这个消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信息,新政府工地出土的文物,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十八具石棺里,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指示一到,工地再次被警戒起来。孙德茂叫苦连天,一日三趟跑郭伟办公室讨要主意。
郭伟能有什么主意?只能一个人闷在办公室里,摔桌子踢凳子,像关在笼中的豹子,焦躁无力。省里的指示就是一道门槛,别说郭伟,就是关书记,也是无能为力。
我在签完了水厂的合同后,全身轻松。带着黄微微在盘小芹的超市里喝了她煲的最后一罐汤,我们准备上路,回衡岳市。
黄微微一连在农古住了一星期,这让我始料不及。像她这样的千金小姐,一日无歌,顿觉天晕地暗,两天无欢,便似日月无光。
倒是盘小芹说了一句让我十分受用的话:这世上万物,都是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的道理。黄微微身份再金贵,在我的面前,也如风中的纸片一样,毫无半点力量。
黄微微的柔情,有时候让我内心也揣然。我郁风何德何能?有美人如此垂青,是祖上修来的福分?人说情场得意,官场便失意。而我倒感觉,有了黄微微,我从秘书到乡长,再从乡长到镇长,也就一年不到的时间。
人在得意的时候往往觉得天高地阔,天下任我纵横。正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再不把全部的爱给了她,良心也会受到谴责。
想法归想法,行动却依然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是怕拒绝,而是潜藏在心底的一个小我,在我每次要付诸行动的时候,总会在我耳边呼喊:“慎重…慎重。”
这个小我,伴着我在农古走过了六个春夏秋冬。也正是这个小我,见证了乡村美女老师纯洁如水一样的爱情。
我决定在回衡岳市之前,去看看薛冰。
校长老远就看到了我,站在校门口笑呵呵地等着我,转身对屁股后面的学生说:“去叫薛老师,说校长找。”
校长跟在我身后,如今我是镇长,他不敢再与我并排走。
在校长办公室坐下不到五分钟,薛冰捏着一本教案匆匆敲门进来,一眼看到我,惊愕得眼睛溜圆,开口便说:“你怎么来了?”
校长很不高兴自己下属的这种语气,训斥着说:“郁镇长是来检查工作的,薛老师你怎么这样说话?”
薛冰恍惚着神色,凄然一笑道:“校长,你要我怎么说话?郁镇长日理万机的人,我们是不是要夹道欢迎欢迎?”
她的话里全部是火药味,让人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算了,你还是去上课。我找郁镇长汇报一下工作。”校长挥手让薛冰离开。她迟疑了一下,转身要走。
我喊住了她:“薛老师,我还有话跟你说,方便吗?”
薛冰黑着脸说:“有什么不方便的?但是要等我下课后再说,你没看到校长叫我去上课吗?”
我转眼看校长,老头子尴尬地笑,搓着双手说:“你们先说,你们先说。你的这节课,我去帮你改,下午放你半天假,你的课都改成体育课,好不好?”
薛冰白了一眼校长,抿紧自己的唇:“有必要吗?”
“有的,有的。我先去帮你改课啊。”校长急匆匆拉开门出去,屋子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她站我坐,空气变得沉闷起来。
“就在这里说?”我问,站起身来:“要不,我们去你房里谈谈吧。”
“不!”她倔强地不肯走:“有话就在这里说,说完了快回去,家里还有个人在等你呢。”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什么意思?”
“还要我说透?黄微微不是来了几天了吗?”她泪水隐隐,似乎要冲破眼眶的束缚。
“我们还是去你的房间说说吧。”我坚持着,想去拉她的手。
她甩开我的手,转身出门。我跟在她后面,朝她的宿舍走。后面校长一溜小跑过来,嘴里喊着:“郁镇长,我还没汇报呢。”
我头也不回地扬一下手说:“等下再说。”
校长停住了脚步,依旧喊道:“我就一个事,镇中学要迁址么?”
我没理他。新政府的迁址现在还挂在半空中,你一个中学,什么都不要想了。
薛冰的房间窗帘低垂,屋子里暗淡无光,屋子里一股陈旧的气息,显然很久没有打开过窗户了。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子房间,居然有这样的景色,显然是心受到了伤害!我的心一颤,愧疚接踵而来。
门一关上,薛冰就扑进我的怀里,嘤嘤哭了起来,转瞬就打湿了我的前胸。
我抚摸着她的背,心里一阵剧痛。
“冰儿,对不起。”我喃喃叫道,嗓子哽咽。
她抬起头,凄然一笑说:“我不怪你。”
她慢慢平静下来,在床边坐下,拿起手边的一件未织好的毛衣,低着头慢慢地织。
“其实我应该早就要想到,你不会呆在农古一辈子,你是个志向远大的人,怎么会甘心在乡下一辈子呢?”她慢慢地说,不时抬起头来看我一眼:“黄微微是个好姑娘,人漂亮,家庭好。父亲还是市委组织部长,能帮到你。我有什么呢?除了一颗心,什么都没有。”
我说不出话来,之前薛冰说过要进行一场战争,现在看来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是我不想要你,做女人的,只要自己心爱的男人有一个好前程,又有什么不能舍得的呢?”
“冰儿…。”我叫她,说不出话来。
“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她安静地看着我,眸子里流露出女人专有的娴静:“我是真心愿意你们好。”
她扬了扬手里正在织的毛衣说:“这件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织,不知道你合不合身。”
我使劲点头说:“肯定合身。”
“试试?”
“好。”
她过来,把毛衣从我头上套下,伸手抻了抻领口,满意地说:“还好,不差多少。”
我闻着她身上飘过来的淡淡幽香,心里一激灵,伸手搂住了她的腰。
她没有挣扎,安静地依在我怀里,微微闭着眼睛说:“最后再亲我一次吧。”——
221、蜜爱
薛冰像猫儿一样倦伏在我的怀里,长长的睫毛覆盖着深潭似的双眸,偶尔微微地颤动,如初翅的蝴蝶,翕动柔软的翅膀。
她的嘴唇噏动着,犹如花瓣一般,等待我去亲吻。
这个曾经给过我无数欢乐的女子,让我在多少个黑夜不知不觉迎来了黎明,这个曾经给过我许多希望的女子,让我憧憬着未来鲜花遍地。
我没敢吻下去,我知道只要我吻下去,我就无法挣脱她的柔情。我本来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只是故意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只有傻瓜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个傻瓜!那样我就可以活得很真,活得胸怀坦荡,活得不需看任何人的眼色,揣摩任何人的心思。
但我不能,这是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我们都在夹缝中求生,我们不得不为生存而隐藏与生俱来的率真和坦荡。
我轻轻地推开她,心里像被插了一把刀,鲜血直流。忍着眼泪,我拉开门,转身要走。
“你就这样走了么?”她在我背后哀哀怨怨地说,哽咽着,似乎要抽泣。
我停住脚步,但我不敢回头,她从后面环抱过来,搂着我的腰,将脸贴在我的后背,任清泪长流。
沉默了一会,我才轻声说:“冰儿,我会想办法调你到市里去。”
“不重要了。无所谓了!”她轻轻地缀泣:“自己心爱的男人不在身边,就是到了天堂,又怎能快活啊。”
“我走了。”我说,想起今天来找她,无非也就是想说这一句话。如今话已经出口了,我顿觉心里像扒开了塞子一样的舒畅。
她放开手,转身扑倒在床上,嘤嘤地哭起来。
我踟蹰了一会,毅然转身离去。
刚到校门口,校长气喘吁吁追出来,拉住我问:“镇长,镇长,你不多坐一会么?”
我强作笑容说:“有事要处理呢。”
校长感叹着说:“到底是镇长,事就是多。镇长啊,你看啊,我们中学也是五十年代的老学校了,这次政府搬迁,有没有考虑一下我们?”
“有啊,”我爽快地说:“镇政府搬到老鹰嘴,剩下老政府,就给你们中学。”
校长惊讶地张大了嘴,嗫嚅半响说:“就这样啊?”
“你还想怎样?”
“原来乡里年年收建校费,建一所中学的钱怕是足够了吧

![[火影柱斑]宇智波斑驯养日记封面](http://www.xxdzs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