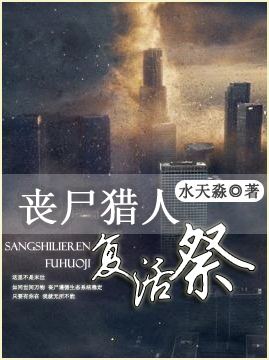复活[列夫·托尔斯泰]-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您安静点儿,”他说。
“我可用不着安静。你以为我醉了吗?我是有点儿醉,但我明白我在说什么,”玛丝洛娃突然急急地说,脸涨得通红,“我是个苦役犯,是个……您是老爷,是公爵,你不用来跟我惹麻烦,免得辱没你的身分。还是找你那些公爵小姐去吧,我的价钱是一张红票子。”
“不管你说得怎样尖刻,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低声说,“你不会懂得,我觉得我对你犯了多大的罪!……”
“‘我觉得犯了多大的罪……’”玛丝洛娃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当初你并没有感觉到,却塞给我一百卢布。瞧,这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可如今我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
“如今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重复说,“我说到一定做到。”
“可我敢说,你做不到!”玛丝洛娃说着,大声笑起来。
“卡秋莎!”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摸摸她的手。
“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尖声叫道,气得脸都变色了,从他的手里抽出手来。“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玛丝洛娃继续说,急不及待地把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出来。“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她霍地站起来,嚷道。
看守走到他们跟前。
“你闹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您就让她去吧,”聂赫留朵夫说。
“叫她别太放肆了,”看守说。
“不,请您再等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看守又走到窗子那边。
玛丝洛娃垂下眼睛,把她那双小手的手指紧紧地交叉在一起,又坐下了。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您想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我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是您的事。我什么也不需要您帮忙。我对您说的是实话,”玛丝洛娃说。“唉,我当初为什么没死掉哇?”她说到这里伤心得痛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玛丝洛娃的眼泪也引得他哭起来。
玛丝洛娃抬起眼睛,对他瞧了一眼,仿佛感到惊奇似的,接着用头巾擦擦脸颊上的眼泪。
这时看守又走过来,提醒他们该分手了。玛丝洛娃站起来。
“您今天有点激动。要是可能,我明天再来。您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玛丝洛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也没有对他瞧一眼,就跟着看守走出去。
“嘿,姑娘,这下子你可要走运了,”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柯拉勃列娃就对她说。“看样子,他被你迷住了。趁他来找你,你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人什么事都有办法。”
“这倒是真的,”道口工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穷人成亲夜晚也短,有钱人想什么有什么,要怎么办就准能办到。
好姑娘,我们那里就有一个体面人,他呀……”
“怎么样,我的事你提了没有?”那个老婆子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伴们的话,却在板铺上躺下来。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墙角。她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她的内心展开了痛苦的活动。聂赫留朵夫那番话使她回到了那个她无法理解而对之满怀仇恨的世界。她在受尽了折磨后离开了那地方。现在她已经无法把往事搁在一边,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而要清醒地生活下去又实在太痛苦了。到傍晚,她就又买了些酒,跟同伴们一起痛饮起来。
49 聂赫留朵夫会见玛丝洛娃后的印象。薇拉的信。聂赫留朵夫回忆同她认识的经过。回忆那次的打猎
“唉,真没想到会弄得这么糟,这么糟!”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走出监狱。直到现在,他才了解自己的全部罪孽。要不是他决心赎罪自新,他也不会发觉自己罪孽的深重。不仅如此,她也不会感觉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直到现在,这一切才暴露无遗,使人触目惊心。直到现在,他才看到他怎样摧残了这个女人的心灵;她也才懂得他怎样伤害了她。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赏,连自己的忏悔都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他觉得再也不能把她抛开不管,但又无法想象他们的关系将会有怎样的结局。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一个戴满奖章的看守露出一副使人讨厌的媚相,鬼鬼祟祟地递给他一封信。
“嗯,这信是一个女人写给阁下的……”他说着交给聂赫留朵夫一封信。
“哪一个女人?”
“您看了就会知道。是个女犯,政治犯。我跟他们在一起。这事是她托我办的。这种事虽然犯禁,但从人道出发……”看守不自然地说。
一个专管政治犯的看守,在监狱里几乎当着众人的面传递信件,这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纳闷。他还不知道,这人又是看守又是密探。他接过信,一面走出监狱,一面看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老练,不用旧体字母,内容如下:
“听说您对一个刑事犯很关心,常到监狱里来看她。我很想同您见一次面。请您要求当局准许您同我见面。如果得到批准,我可以向您提供许多有关那个您替她说情的人以及我们小组的重要情况。感谢您的薇拉。”
薇拉原是诺夫哥罗德省一个偏僻乡村的女教师。有一次聂赫留朵夫跟同伴去那里猎熊。这个女教师曾要求聂赫留朵夫给她一笔钱,帮助她进高等学校念书。聂赫留朵夫给了她钱,事后就把她忘记了。现在才知道她是个政治犯,关在监狱里。她大概在监狱里听说了他的事,所以愿意替他效劳。当时一切事情都很简单,如今却变得那么复杂难弄。聂赫留朵夫生动而愉快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同薇拉认识的经过。那是谢肉节之前的事,在一个离铁路线六十俄里的偏僻乡村。那次打猎很顺手,打死了两头熊。他们正在吃饭,准备动身回家。这时,他们借宿的农家主人走来说,本地教堂助祭的女儿来了,要求见一见聂赫留朵夫公爵。
“长得好看吗?”有人问。
“嗐,住口!”聂赫留朵夫板起脸说,从饭桌旁站起来,擦擦嘴,心里感到奇怪,助祭的女儿会有什么事要见他,随即走到主人屋里。
屋子里有一个姑娘,头戴毡帽,身穿皮外套,脸容消瘦,青筋毕露,相貌并不好看,只有一双眼睛和两道扬起的眉毛长得很美。
“喏,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这位就是公爵,”上了年纪的女主人说,“你跟她谈谈吧。我走了。”
“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哇?”聂赫留朵夫说。
“我……我……您瞧,您有钱,可您把钱花在无聊的事上,花在打猎上,这我知道,”那个姑娘很难为情地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益的人,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因为什么也不懂。”
她的一双眼睛诚恳而善良,脸上的神色又果断又胆怯,十分动人。聂赫留朵夫不由得设身处地替她着想——他有这样的习惯,——立即懂得她的心情,很怜悯她。
“可是我能为您出什么力呢?”
“我是个教员,想进高等学校念书,可是进不去。倒不是人家下让进,人家是让我进的,可是要有钱。您借我一笔钱,等我将来毕业了还您。我想,有钱人打熊,还给庄稼人喝酒,这样不好。他们何不做点好事呢?我只要八十卢布就够了。您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她怒气冲冲地说。
“正好相反,我很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这就去拿来,”聂赫留朵夫说。
他走出屋子,看见他那个同伴正在门廊里偷听他们谈话。
他没有答理同伴的取笑,从皮夹子里取出钱,交给她。
“您请收下,收下,不用谢。我应该谢谢您才是。”
聂赫留朵夫此刻想起这一切,感到很高兴。他想到有个军官想拿那事当作桃色新闻取笑他,他差点儿同他吵架,另一个同事为他说话,从此他同他更加要好,又想到那次打猎很顺手很快活,那天夜里回到火车站,他心里特别高兴。双马雪橇一辆接着一辆,排成一长串,悄没声儿地在林间狭路上飞驰。两边树木,高矮不一,中间杂着积雪累累的枞树。在黑暗中,红光一闪,有人点着一支香味扑鼻的纸烟。猎人奥西普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从这个雪橇跑到那个雪橇,讲到麋鹿怎样徘徊在深雪地上,啃着白杨树皮,又讲到熊怎样躲在密林的洞穴里睡觉,洞口冒着嘴里吐出来的热气。
聂赫留朵夫想到这一切,想到自己当年身强力壮,无忧无虑,多么幸福。他鼓起胸膛,深深地呼吸着冰凉的空气。树枝上的积雪被马轭碰下来,撒在他脸上。他感到周身暖和,脸上凉快,心里没有忧虑,没有悔恨,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望。那时是多么快乐呀!如今呢?我的天,如今一切都是多么痛苦,多么艰难哪!……
薇拉显然是个革命者,她因革命活动而坐牢。应该见见她,特别是因为她答应帮他出主意,来改善玛丝洛娃的处境。
50 聂赫留朵夫初访玛斯连尼科夫。获准在监狱办公室跟卡秋莎和薇拉见面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回想昨天的种种事情,心里不由得感到害怕。
不过,心里虽然害怕,他还是更坚强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开了头的事做下去。
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走出家门,乘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要求准许他到牢房探望玛丝洛娃,以及玛丝洛娃要他去探望的明肖夫母子。此外他还想要求探望薇拉,因为她可能帮玛丝洛娃的忙。
聂赫留朵夫在团里服役的时候就认识玛斯连尼科夫。玛斯连尼科夫当时任团的司库,忠心耿耿,奉公守法,除了团里和皇室以外,天下什么事也不关心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什么事也不想过问。聂赫留朵夫发现,他现在已当上行政长官,他所管辖的已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省和省政府。他娶了一个既有钱又泼辣的女人,那女人逼得他脱离军队,改任文职。
她一会儿嘲弄他,一会儿又象对驯服的小猫小狗那样抚爱他。聂赫留朵夫去年冬天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但他觉得这对夫妻十分乏味,以后再也没去过。
玛斯连尼科夫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满面笑容。他的脸还是那样又胖又红,身材还是那样高大,衣服还是象在军队里一样讲究。以前他总是穿一身款式新颖的军装或者制服,干干净净,紧包着他的肩膀和胸部;如今他穿着时髦的文职服装,也是那样紧包着肥胖的身子和宽阔的胸膛。今天他穿着一身文官制服。他们两人虽然年龄悬殊(玛斯连尼科夫已近四十岁了),但彼此还是不拘礼节,你我相称。
“啊,你来了,真是太感谢了。到我太太那儿去吧。我此刻正好有十分钟空,过后要去开会。我们的上司出门了。省里的事现在我在管,”他说着三才又作“三材”。中国古代哲学术语。①指天、地、人,,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神色。
“我有事找你。”
“什么事啊?”玛斯连尼科夫仿佛一下子警惕起来,用惊恐而又有点严厉的音调说。
“监狱里有一个人我很关心(玛斯连尼科夫一听见‘监狱’两个字,脸色变得更严厉了),我很想探望,但不要在普通探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封面](http://www.xxdzs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