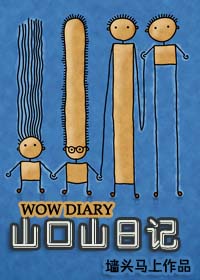小偷日记-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每天只挣10法郎,”他对我说,“我对巴黎人傲慢的嘴脸实在不敢恭维。”
他还给我讲了其他一些细节,我来不及在这里赘述。我一直爱着他。他的品质(犹如扎瓦的品质)令人联想到某些毒品、某些气味。虽然不敢说是美味好闻,但却容易上瘾,很难摆脱。
我已经不等阿尔芒了,可他却回来了。我进门发现他躺在床上,正抽着烟。
“你好呀,小伙子。”他首先向我打招呼。
他第一次主动伸手握我的手。
“怎么样,过得不错吧?没出什么乱子吧?”
我曾经谈起过他的嗓音。我现在似乎觉得他说话的声音和蓝色的眼睛一样冷若冰霜。他不论是看人或看东西,目光都专注,他说话也一样,好像是用假嗓子,漫不经心地同人交谈。有些眼神,可以说光芒四射(如吕西安的,史蒂利达诺的,扎瓦的),阿尔芒则没有这样的光芒。他的嗓音也没有多少光彩。在他心灵深处,真正为他播音的是一小撮小人,他一直为他们保守着秘密。这声音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不过,人们从他的声音里,多少辨认出一点阿尔萨斯的口音:他心目中的人物原来是德国佬。
“对,过得不错,”我回答说,“我看管着你的东西,你看。”
直到今天,有时我还希望警察把我叫住对我说:“我看没错,先生,偷东西的不是您,真正的罪犯已经逮起来了。”但愿我一生清白无辜。刚才我回答阿尔芒的话时,真巴不得让他知道,若是换了一个人——这个人当然还是我——早把他的行李偷走了。我浑身战栗着为我的忠诚庆功。
“哦,这个嘛,我相信。”
“那你呢,好吗?”
“哦吗,是的,还行。”
我壮着胆子坐到床沿上,把手放在毯子上。今晚,灯光从高处照下,更显出他的青春活力和健美的肌肉。我突然发现有摆脱尴尬和烦躁的可能性,史蒂利达诺和罗贝尔的暧昧关系把我弄得狼狈不堪。阿尔苦不一定爱我,但只要他允许我爱他就行,阿尔芒很可能是我的救星,他不论从年龄上还是从精力上都占上风。他来得正是时候。我对他爱慕不已,侧着脸,准备贴在他那毛茸茸的胸膛上温存一番。我的手向前摸去。他笑了。他第一次对我微笑,这就足够了,我爱他。
“我可没有干过坏事。”他说。
他侧过身去。一阵轻微的紧张提醒了我,我巴不辱得到他可怕的大手,眼看那只手就压下来要抚摩我的头。这个武断的手势明明告诉我,他让我俯身为他行乐。今天我恋爱了,也许有点勉强,目的就是要他大动肝火,希望他更加喜欢我。
“我想喝一杯。我马上就起来。”
他下了床,穿好了衣服。我们一下到街上,他就称赞我与男色鬼周旋次次都干得非常漂亮。我大吃一惊。
“是谁告诉你的?”
“你别管他是谁。”
他甚至知道我捆绑过一个色鬼:
“真是出手不凡。想不到你还有这下子。”
于是他告诉我,码头上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伎俩。每个受害者都提醒别人或前来过夜的码头工人,要他们提防我(他们经常同男色鬼走在一起)。我现在已经成了同性恋者无人不知和谈虎色变的人物。阿尔芒来得很及时,使我知道了我已名声在外,这对我显然是一种危险。他一回来就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即使史蒂利达诺和罗贝尔现在还蒙在鼓里,但很快就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
“你干得很好,小家伙。我很高兴。”
“哦,这不难。他们是窝囊废。”
“干得很好,我说的。我真没想到。喝酒去。”
回到房间后,他对我一无所求,我们很快就睡着了。那以后,我们经常见到史蒂利达诺。阿尔芒认识了罗贝尔,并对他一见钟情,但罗贝尔这小子略施小计就把阿尔芒给甩开了。一天,阿尔芒笑着对他说:
“你有了让诺,难道还不够?”
“他嘛,不是一回事。”
自从阿尔芒知道我夜间胆大妄为之事之后,他事实上已经把我当哥们看待了。他同我说话,给我出主意提建议。他对我的蔑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母爱般的温情和关怀。他甚至管起我穿衣戴帽的事。晚上,我们抽完烟,他祝我晚安后,倒头就睡着了。我深感遗憾,睡在我的所爱身边,却不能花样翻新,巧施妙计,使出爱抚的绝招来向他证明我的爱。他对待我的友好方式,迫使我严肃认真,不敢越雷池一步。尽管我也承认,在我的胡作非为中有诈骗,在我的胆大妄为中有恐惧,但我仍然百倍努力,争取当一个不负阿尔芒重望的男子汉。我想,常规举动与英雄壮举格格不入,不应该相提并论。就那么简单,阿尔芒无论如何不会答应我供他鱼水之欢。出于对我的尊重,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利用我的肉体。殊不知,他越利用我的肉体,我浑身就越充满力量和勇气。
史蒂利达诺和罗贝尔靠西尔维娅挣的钱生活。罗贝尔似乎已经把我们同男色鬼鬼混的卑劣伎俩忘得一干二净了,对我干的那一套装出根本瞧不起的样子。
“你把那玩意儿也叫差使?还当美差呢。”一天,他对我说,“你攻击那些支着硬领、拄着拐杖才能站立的糟老头子,算什么能耐!”
“他自有道理。最好是选好对象嘛。”
我没有想到,阿尔芒的这句反驳会接连带来一场精神上最大胆的革命。罗贝尔还来不及回敬,他语重心长地来了个长篇大论:
“比如我吧,你认为我该怎样下手?”然后又转向史蒂利达诺说道:“你认为如何是好?我嘛,只要有效果,你听着,我下手的对象可能不是老头,而是老太婆。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我选择最软弱无力的人。我要什么东西,是钱。成功就是美差。你什么时候明白了,光靠骑士精神干活是不行的,你就算肚子里有货色了。他(阿尔芒从不叫我名字或昵称,而是用手指我),他已经超过了你们,他是对的。”
阿尔芒的声音没有颤抖,可我激动得无法自持,担心他会把惊天动地的秘密结抖了出来。他最后一句话掷地有声,总算让我放了心。他不开口了,我心里却百感交集(无边愧海开浪花),声声责备我屈服于外表的虚荣。此后,阿尔芒再也不提这个话题(史蒂利达诺和罗贝尔也都不敢论战),但这道命题却在我思想中植下了胚芽。从此,在我看来,地痞流氓特有的荣誉法规是多么滑稽可笑。在我的精神领域里,阿尔芒逐渐成了法力无边、至高无上的主宰了。我不再把他看成一个整体,而是把他想象成一笔经过千辛万苦磨练出来的经验积累。然而,他的肉体仍然那么厚实,我喜欢他能保护我。我在一个从不露惧色的男人身上——我相信如此——找到了这样的权威,顿时感到思路新奇,兴高采烈。毫无疑问,不久我就决计深入开发和丰富这种种暧昧的感情,愉悦中夹杂着羞辱,发现自己原来是相反相成的集大成和大本营,但我已经预感到,该由我们申明哪些东西可以当作原则来使用。我的意愿被阿尔芒的思考和态度剥去了道德面纱,后来,我如愿以偿,非常重视与警察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我是在马赛遇见贝尔纳蒂尼的。彼此渐渐熟悉了,我就叫他贝尔纳。在我眼里,只有法国警察才称得上神通广大。我当时22岁,而贝尔纳已经30岁了。我想精确地还原他的本来面貌,但我的记忆鞭长莫及,只保留了他给我留下的肉体和精神力量的最初印象。当时,我们都在杜巴诺街的一家酒吧里。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指着他向我推荐。
“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叉杆掮客,”他说,“他身边总有几个花枝招展的女人。”
当时陪他的那个姑娘看起来很漂亮。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警察,即使与他擦肩而过我也会视而不见。欧洲各国的警察真叫我害怕,所有小偷对此感同身受,而法国警察尤其令我胆战心惊。究其根源,与其说是灾难性错误造成我身临绝境,倒不如说是我天生的、无法改变的犯罪感在作怪。同流氓世界一样,警察世界我从来不敢问津,我头脑清醒(有悟性),岂敢跟警方厮混在一起。要知道,警察世界是一群行踪不定、东奔西跑、腾云驾雾的队伍,处于不断组建过程中,司空见惯却神出鬼没。其中穿警服的摩托队我们都认为是警察的代表,力量的标志。别国的警察且不说,反正我认为法国警察是这样。也许是因为言语相通的缘故,我发现了许多深不可测的黑洞。(它已不再是一支社会的组织,而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力,它直接震撼着我的心灵,搅得我心神不定。只有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警察能够真正做到警匪一家。这一威力无比、相反相成的综合体,这千真万确的庞然大物,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胆战心惊。它的强大磁场,长期把我们吸引得神魂颠倒,搅得惊恐万状。)
贝尔纳蒂尼也生活在人世间,看得见摸得着,很可能是一个恶魔组织的昙花一现。这个组织像葬礼葬品一样令人恶心,然而却名扬天下,可与帝王的荣耀相媲美。我看了看他,浑身颤栗起来,发现在这普通的皮囊里有一片我一直求之不得的风水宝地。他有点像过去的鲁道夫·瓦伦迪诺,一头黑发紧贴着头皮,油光可鉴,往左分留出一道又直又白的头路。他很强壮。他的脸面粗糙,有点像花岗岩,我需要他既粗暴又残酷的灵魂。
渐渐地,我体会出他的美。我甚至认为,是我创造了他的美,从警察的概念出发,裁定他美就美在这张脸上。在这个肉体上,警察本来就应是这个样子。对整个警察组织,民间有一种说法更增加了我内心的混乱:
“秘密警察局。他是秘密警察。”
此后我每天设法巧妙地跟踪他,远距离跟他照面。我像春蚕一样吐一根细丝缠着他。他不知不觉被我拉进了我的生活天地。后来我到底离开了马赛。我暗地里却保存着对他一片痛苦又温柔的回忆。两年后,我在圣夏尔车站被捕。警察们对我非常粗暴,指望我能招供点什么。警察局的门打开了,我感到大吃一惊,进来的是贝尔纳蒂尼。我害怕他变本加厉对我进行严刑拷打,可他却让他们停止用刑。我恋恋不舍跟踪他时,他从来就没有注意过我。他可能跟我打过两三次照面,两年过去了,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之所以让我免受皮肉之苦,决不是出于同情和好心。他跟别的警察一样,凶狠得很。我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保护我。两天后,我被释放了,我设法见到了他。我对他表示感谢。
“您,不管怎么说,您干得很漂亮。”
“哦,很正常。何必折腾你们这些小伙子呢。”
“跟我喝一杯去。”
第八节
他接受了。第二天,我又遇见他。这次是他请我。酒吧间只有我们两个顾客。我的心怦怦直跳,说:
“我认识您很久了。”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喉咙发紧,怕他生气,我索性向他吐露了我对他的爱慕,承认自己为了追随他不知要了多少花招。
他笑了起来,说:
“是吗,你对我一见钟情?那现在呢?”
“还有一点。”
他笑得更开心了,可能受宠若惊吧。(扎瓦最近向我承认,得到一个男人的爱和赞美比得到一个姑娘的爱和赞美更值得他骄傲。)我就站在他身边,多少带点油腔滑调对他谈情说爱,惟恐严肃的语气会提醒他执行

![[火影柱斑]宇智波斑驯养日记封面](http://www.xxdzs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