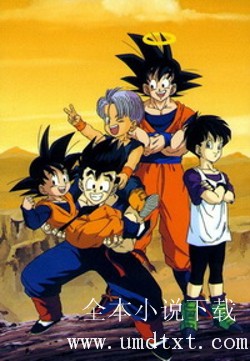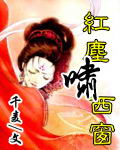西窗烛话-第1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蚂蚁般忙碌的矿工,黑得发亮的煤炭倾倒在河边,等着用船运走,都是一些不大的货轮,皮带机在转动着,班车再向前走,可就是秭归的地盘了。
如今,峡口镇已不存在了,随着三峡大坝蓄水,兴山县城也迁到古夫镇去了,那么美丽的高岚风景区呢?
六六大顺 59.屈原故里
沿着香溪河下行5公里,就是屈原故里,地名就叫屈原,没下过车,坐在班车上没发现这里与其它地方有什么特殊之处,好奇地向乘客打听,方知真正的屈原故里长乐坪不在公路边上,还得翻山越岭的走上一段路,原来屈原也是山野中人,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也有一种飘飘然的神仙风度。
再向前就是长江边了,一边沿香溪河,一边沿长江,背靠巍巍群山,一长排建筑就构成了精巧的香溪镇,不大,依山而建,有些做生意的门面,长江边有一座码头,也有一个汽车轮渡,记得有一年我曾在此住过一夜,一栋小楼的二楼,推开窗户,江风迎面拂来,沁人心扉,香溪河就平缓的投入大江的怀抱。
顺江上行不到10公里,就是秭归县城归州镇。这是一个靠在长江边山坡上的古城,很有层次的层层向上,公路沿着之字形道路在红砖灰瓦的房屋之中穿行,道路是平坦的,但连接两条街道之间的小巷狭窄而陡峭,像迷宫似的,与巴东有异曲同工之妙,江边是一排排破旧但有韵味的吊脚楼,
小城里人山人海,商店里总是荡漾着流行歌曲的旋律,这里的菜里面已经像四川人那样很喜欢放辣椒了,只要是饭馆,就总是飘着一股呛人的辣味,山里人很好辨认,男的都叼着叶子烟,光头上扎一个白帕子,女人们眼睛不够用了,什么都好奇,什么都要看,一笑就露出了四环素的黄板牙。
带着妻儿与侄子从兴山来到秭归,住在县招待所里,然后和他们上街乱转,结果我们找到了一座已经破损得很严重的老城门洞,厚重的青石条,想来也曾经有过很多故事,有座郭沫若题写匾额的“屈原故里”的木牌坊,奇怪的是,另一座“昭君故里”的木牌坊也在此处,所谓相映成趣,实际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经常出差经过秭归,来去匆匆,更多的时间就坐在江边的吊脚楼上,那里多有很小的酒馆,厨房向着弯弯曲曲的小巷,饭桌就放在靠长江的窗旁,隔着柔软的沙滩,炒上两个菜,打上一杯酒,慢慢的看长江里百舸争流,汽笛声声,倒满有情趣的,有一次心血来潮,原本是下水返宜,却乘船上行到巴东去了。
屈原祠(大家都叫屈原庙)在城外的高山上,临江而建,山门是一面17米高的牌楼,匾额既有“孤忠流芳”的赞誉,又有“光争日月”的夸耀,前者恰如其分,后者就夸得过分了。整个建筑气势磅礴,被满山的桔林相依偎,里面有纪念馆,还有长长的碑林,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院中的那尊忧国忧民的屈原铜像,微皱的眉头,消瘦的面容,花白的鬓发,凝重的神情,右手按住剑柄,长跑随风飘动,自认为这是宜昌雕塑界最成功的作品,至少也是最能传情达意的成果了。
祠后有屈原大夫的衣冠墓,通过墓室门上的玻璃望进去,就是一副大红棺材而已,油漆装饰的很仔细罢了。屈原也真够固执的,孤芳自赏的写一些《桔颂》、《天问》、《离骚》也就罢了,被楚国之君由苏州发配到湖南汨罗还痴心不改,坚持自己的主见,最后只好投江自尽了,这也是死谏的一种,只是过于悲壮了。
郭沫若后来在陪都重庆据此写了一部借古讽今的话剧《屈原》,很久以前一目十行的翻看过话剧剧本,除了有几处精彩独白以外,也就平常,不理解当时何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还是喜欢陆游的那首小诗:“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就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惟有涛声似旧时。”入木三分,写得好极了。
乘船在这段江里上下不知多少次,只记得群山巍峨,高不可攀,尤其是面朝长江的这一面,很多地方都被岁月和雨水剥落成悬崖峭壁,夕阳将晚霞洒在山壁上,整条江就像被镀上了一层金黄,那么华贵,那么庄重,过眼不忘,江水翻腾着,有些浑浊的江水的漩涡巨大无比,船驶近了,漩涡又消失了,神奇极了。
秭归境内的兵书宝剑峡看过无数次,最终也没看懂,也许是我没有找到兵书和宝剑的位置,更不消说牛肝和马肺是什么样子,说来惭愧,至今我也不知牛肝马肺长成何样,还是大滑坡后的新滩叫人触目惊心,不是亲临其境,绝不能想象几乎半面山坡全部滑落下来的场景,那是一种震撼,一种大自然威力的显现。
在香溪河口乘班车渡过长江,就是江南了,一条道路沿着一条小河走到郭家坝镇,就开始爬山,步步上坡,山越爬越高,也就离长江越远,车外的景致也就越荒凉,先是砖瓦房消失了,厚重的土屋的周围还有些旱田,再后来就是一些石屋了,不知为什么,不少的石屋的屋顶都被揭去了,光秃秃的,很伤感的。
班车一直在荒凉的大山深处盘旋,从山脊上转来转去,柏油路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变成了石渣路,道路也算平坦,只是灰太大,只要有人上下车,司机就会停车,开门,尾随在车后的尘土就会乘机扑进车厢,黄色的烟雾就会弥漫在乘客之间,呛人的很,每个人都用袖口,或是手掌捂住口鼻,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过了杨林桥镇,就是长阳县的堡镇了。
六六大顺 60.木桥溪、钟离山、招徕河(上)
长阳由于大山的阻隔,就形成了很独特的地理风貌,交通被明显的分为两部分,一条是沿318国道前行,以后的宜(宜昌)万(万州)铁路和沪(上海)蓉(成都)西(西藏)高速也沿用这条走道,当地人称之为前河;另一条沿清江前行,不过随着隔河岩水电站的建成,那条被当地人称之为后河的地方更重视水上交通了。
所谓条条道路通长安,进入长阳也有不少方法,我走得最多的就是从土城翻越赤土垭,当汽车都被陡峭的上坡折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就上了赤土垭了,司机总喜欢在此停车检查一番,年轻的“一把火”在一棵大树背后解完小便,一边拉着裤子上的拉链,一边问我:“王哥,到哪里吃饭?”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很庄严的映照着远近的千山万壑,我一直无法理解对面山腰上的人家是如何生存的,那些灰瓦土墙后面的山民是如何守着几块贫瘠的田地,习惯于那么寂寞而枯燥的生活的,我也放光了肚里的浊水,从另一边登上敞开车门的东风140大货车的驾驶室,咕噜了一句:“还是到木桥溪再说。”
一路下坡,汽车车厢发出轰轰隆隆的声响,司机不停的按着喇叭,催促着前面的一辆农用车让道,乘着那辆车向路旁稍稍靠边的一刹那间,我们已经轻快的超到前面去了,坡下就是高家堰镇,沿着公路而建有几家商店,一排镇政府机关,一个农行营业处,有两家卖肉的,还有饭馆,旅店,邮电所,拐弯处有座大桥,桥边稀稀拉拉的也有些卖菜,卖水果的小摊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座林业检查站了。隔着老远就能看见那大大的警示牌,还有那道红白相间的栏杆,虽然每次从此经过,都能看见有车被拦住,停在路边接受检查,货主跟在检查人员后面苦苦哀求的模样,我们却很顺利,出示购货发票,与相识的检查人员打个招呼,递上一支烟,也就放行了。
有一次,木桥溪供销社的肖主任称发票还没有到总社去领,但已经给检查站打过招呼了,保证让我安全过关,他拍着胸说:“放心,我都打好招呼了。”本来我还有些犹豫,但天色已晚,加上又开始下雨,就决定开车离去,车从两山对峙的木桥溪钻出山来的时候,我就有些忐忑不安了。
事实上,细雨朦朦中望见那盏警示的红灯时,我就有些心虚,当那个检查人员将我们装得满满的山桂竹的货车拦停在路边时,我就感到大事不妙,因为那个检查人员陌生的很,走进人声沸腾的检查站里一看,更是大吃一惊,居然站里今天一个人也不认识,心就一个劲的向下坠,
检查站的新人们铁面无私:“销售发票?”我在摇头;“出口许可证?”我还是摇头,“没收!”我小心翼翼的解释:“供销社不是打来电话说明了情况?”“没听说。”我在请求他们是否网开一面,回答得倒也干脆:“罚款!”我有些傻眼了,至少还有十几个与我同样遭遇的货主焦头烂额的坐在检查站的长条椅上一筹莫展。
我就到旁边的邮电所给肖主任打电话,接线的小姑娘噘着嘴试着给我接了好几次,谢天谢地,最后终于接通了,杂音很大,可以听见山谷里的风在电线上刮过的呼啸声,但我还是听清了肖主任那嘶哑的嗓音。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也很震惊,因为没听说过检查站换人的风声,但我沮丧得仿佛看见了他那张得意的脸在笑。
我要他马上开来销售发票,他却说镇供销社的会计不在家,我向他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却把话题转到我还没有付清的好几千元的购竹款上了,我知道他这是下井落石,便开始愤怒了起来,我警告肖主任赶快赶到高家堰来,向他们解释清楚,如果我在两个小时后还看不到他的出现,我就乖乖的缴纳罚款,然后从购竹款里面扣除。
我不知道我的威胁是否会产生效果,但我注定他会就范的,因为那几千元钱就是他的政绩,他不会轻易放弃的,于是就带着司机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吃晚饭,仔鸡火锅烧得很好,喝了一点酒,三个人就把一锅香喷喷的鸡块消灭得干干净净,同时也知道了,检查站里的那帮陌生人是林业稽查的,今晚突然袭击高家堰,我们是撞在枪口上了。
肖主任果然赶来了,是搭别人的摩托出山的,那天晚上,我跟着他找人帮忙,先是镇上供销社的头头,再通过他们找到林业站的头头,几经周折,我们最终被那些林业稽查的极不情愿的放行了,货车在漆黑的夜幕中轰鸣着穿过层层细雨,向宜昌进发,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杨白劳居然不怕穆仁智的快感。
从高家堰到点兵河虽然两边山高林密,山谷里却是一段又平又直又宽的大道,汽车走在上面,油门一踩到底,风驰电擎的,别提有多爽了,据当地人称,当年修建这条路的时候,正是准备打仗的紧要关头,李先念命令要能在公路上起降军用飞机,于是就有了这样宽阔的道路,大概是有道理的,要不在大山深处,为何要劈山炸石,搞出这么大的场面,连后来的宜黄高速也自叹不如。
木桥溪就是公路边的一个小居民点,贴着右侧的山麓,有些低矮的平房,后来又有了些简陋的两层楼房,一色的白瓷砖,与漆黑的老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供销社与我们做生意,是在农资公司办的一家餐馆里吃的饭,几个长相丑陋的女人与肖主任打情骂俏,热闹极了。
我固定在一家姓冯的小餐馆里吃饭,首先吸引我的是冯哥做得一手好豆腐,好吃极了,冯哥高大但沉默寡言,客人上门,就坐在灶门口向里面添柴,没客人的时候,就扛着锄头下地干活,他家的地离小店还得趟过隔着公路的前河,那里有几亩薄田,种些包谷、土豆,后来来得多了,也就熟悉了,就叫他也到桌上来一起喝酒,他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