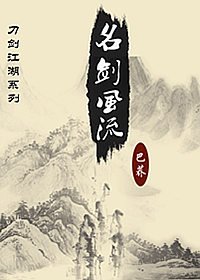状元风流-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秦小姐一听这人出言轻佻,不禁柳眉轻挑,横剑而出,道:“你这登徒子,胡说八道,再是如此轻浮之言,当心本小姐手中宝剑。”
贺山见此,顿时骇然,拉了拉陈尧咨的衣衫,见他褴褛不堪的,心中疑惑,道:“一夜不见,你怎生变的这般模样了?”
陈尧咨听他此言,顿时气从心来,很很的瞪了他一眼,没好气的道:“你还说,我要你二人找的绳索、墙梯,这绳索在何处,墙梯在哪里,你就在这小院转悠了一夜吗?”
范浱听他此言,忙的点头急道:“现在哪有心思论这些,你现在不是已经完好无损的回来了么。可贺山却是……”说到此,再也没说下去了。
陈尧咨一听,这是什么话,这一夜凉风的,就这般轻易地揭过了,想及于此,怒声道:“我完好的回来,我还要去衙门报道呢……”说道此,见他说起贺山,不禁奇道:“贺山出了事,他真么机灵能有何事?”
范浱见他疑惑不已,’唉’叹了一声,无力的坐在石凳之上,双手抱脚的,道:“贺山昨夜为了去寻墙梯,在书院寻了半个时辰也全无,便与我商议,让他走道书院山下街上去借一些,也好有个方便。我在此等了许久也没有消息。今儿一早,便去派人去打听,才传回话说,贺山被知府抓住,说是党项潜入细作之人,知府衙门就要定罪上报朝廷了。”
范浱说起此言,不禁暗自叹息,这贺山与他虽是才相识几年,却是投缘之极,而今贺山被官府拿住,就要定罪,这一时之间,怎能不让他心酸。
陈尧咨从不过问贺山的私密之事,如今贺山到底是否乃是党项奸细,却是让他疑惑不已。这章知州主事,怎能如此轻易的便放过了,陈尧咨知觉浑身如寒意侵袭,这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24章 再见贺山
贺山是否是党项之人尚且说不清楚,这是否是细作之人,陈尧咨更是难以澄清,这个中曲折,只有贺山自己才知晓了。
陈尧咨细细思索,不禁想起了昨日与他比试的章公子,这才过一夜,难道便要变了阴阳,颠倒了乾坤,这章公子便沉不住气了,等不及的要还以颜色么。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这章公子与他,似是有些难解开的结了,这一番贺山能被抓进了衙门,可是少不得要争锋相对一回了。
范浱见他似是没有反应了,不禁急切的道:“嘉谟,你倒是想办法,这一言不发的能有法子么?”
秦小姐见他二人这般模样,不觉心下疑惑了起来,看了看他,道:“你真是陈尧咨?”
陈尧咨听闻她此言,不禁又是一番白眼,憋了憋嘴,没好气的道:“本少爷虽不是万贯家财,还不至于欺瞒你这般的小丫头吧。”
秦小姐一听这陈尧咨呼她小丫头,不觉心急火起,顿时手握宝剑的就冲了上来,剑尖直指着陈尧咨而来,这湘绮绣群随风的摆动,带过这石桌上的一碗茶,登时的就往地上掉了下来。范浱眼疾手快,忙的闪身而去,接在手中。这茶水溢出,烫的这范浱忙的放在地上,把手放在嘴边急忙的哈着气。
秦小姐转眼一看,这清茶无恙,顿时又是火气上来,圆滑的酥胸似是海潮起来,汹涌澎湃,手中宝剑已是离陈尧咨不到三寸,娇嗔呵斥道:“谁是小丫头,你这寒的臭小子,本姑娘比你大的多了。你今儿不给本姑娘说清楚了,定要让你去对簿公堂。”
陈尧咨看了看范浱,范浱也看了看他,突然猛的抓起茶杯,自顾的喝了起来,似是没有见到此景一般,这茶水倒出,没了一滴,他便两个指头抓起了一笑撮茶叶,直往嘴里塞去。
陈尧咨看的这一幕,不禁拉着自己那衣袖,猛的擦了擦眼睛,似是不敢置信一般。
秦小姐见他如此的插科打诨,不禁又是娇声道:“你这小子,到底说清楚了。”情急之下,手往前伸,这宝剑又是前去一寸多。
陈尧咨见此,忙的双手胸前急摆,嘿嘿的道:“姑娘贤惠有理,淑仪矜持,怎会是小女子呢,此乃大家闺秀之风范,世家小姐之雅致也。”
秦小姐听了此言,才放下宝剑,抬头看着这枫叶得意的摇了摇头,道:“算你还不是愚蠢的没法救了,本姑娘不与你计较这些了。”自是陈尧咨才心下松了一口气之时,这丫头又是宝剑扬起,娇声呵斥的道:“即便如此,你还得去衙门,依我大宋律法处置。”
陈尧咨见这剑又一次的扬起,不禁又是一颤,顿时脸上泛起嘿嘿的笑颜,道:“姑娘放心,即是你不让我去,这衙门,我也得走走上一回了。”
秦小姐不觉疑惑道:“这是为何,难不曾你住在衙门?”
范浱顿时无奈的憋了憋嘴,咬了咬牙,深呼了一口气,道:“姑娘,我们朋友被抓,我们不去救他,你说谁该前去?”
秦小姐见这大块头的家伙插言,不禁刷的一声,剑指过去,瑶鼻轻哼的道:“原来是你二人还有同伙,这回可是一举擒获。”
陈尧咨不禁无奈之极,摊上这么号人,谁能不气结,猛的摇了摇头,清醒了一下思路,看着她道:“我们要去公堂,姑娘不是也要前去么?”
秦小姐听他说话,这宝剑又是刷的一声,指向他而来,娇声道:“你这登徒子,早该抓到衙门里去,夹拶子,打板子,上木枷,刺配流放。什么‘风流公子,’我看这‘下流胚子’名号正适合你。”陈尧咨闻此,不觉摸了摸自己的脸,却是带出面上丝丝灰尘。
范浱见此不禁暗自拍了拍胸脯,似是松了松气,暗道还好这宝剑没有刺了过来,否则可就是流血五步,伏尸一人了。
见她说的没完了,陈尧咨不禁疾声道:“你说完了没有?”
这俏小姐见她发火起来,不禁一愣,随即娇声回道:“你想如何?”
陈尧咨看了看她,对范浱道:“我去梳洗一番,咱们便赶往这牢狱,去看看贺山。”说着,便轻轻的拨开这剑尖,往屋子里去了。
这秦小姐倒是没在挥舞着宝剑,看着他往屋子而去,也再没跟上来。
范浱不禁疑惑道:“嘉谟,咱们不去州府衙门,去牢狱做什么?”
陈尧咨不由得笑道:“你这人,比这小丫头还笨。咱们不去寻贺山,能知晓他到底是不是细作吗?”
范浱顿时猛的一醒,道:“对啊,此计甚好。”说着,便喜滋滋的又抓起茶叶,又是往嘴里送去。
…………
陈尧咨换了身衣衫,草草的梳洗了一番,便与范浱、秦小姐二人往这监牢而来。这秦小姐非要把他抓到府衙见官,陈尧咨难以摆脱,便由得她去了,只要不惹麻烦,也就懒得理会。
来到监牢,范浱拿出些银两给这狱卒,便放了二人进去,陈尧咨与范浱往贺山所羁押的刑狱牢房走来。贺山便是被关押在最里的圆木房之内。
狱卒打开这桩门,便让他三人进了去。陈尧咨一见,这贺山正是席地而坐,衣衫褴褛,想必皮肉之苦尝试了一些,此时身上裹着一张草席,目光呆滞的看着眼前,似是毫无察觉。
范浱见此,不禁急忙的跑过去,扶起他双肩,急道:“贺山、贺山……”
叫了几声,贺山呆滞的目光似是突然泛起精光,急忙的抬头,只见乃是陈尧咨、范浱二人,不禁又是地下了头,却是凄凄之声传来,双手紧紧地抓着草席。
陈尧咨见此,不觉心酸不已,他与贺山主仆二人已是三年多,见两人在一起,时常喜笑颜开,在他记忆里,哪有如此悲伤的时刻。
范浱扶起贺山,让他坐在墙角边,急切的道:“你不是去找墙梯么,怎么会成了细作之人,这是为何?”
贺山微微摇头,没有说话,却是看着陈尧咨问道:“少爷,贺山与你相交三年,三年之期已过,却未曾离去,少爷可知这是为何?”
陈尧咨摇了摇头,他还真想不出,这一晃已是三年多,他也从十一岁的小童长了十四,来年便是十五之龄。这时日匆匆而去,到底贺山来历,他却是一无所知。
贺山泛起微微的笑意,道:“少爷从不问贺山这些,贺山也从不相告,此也是不得已之处,还望少爷海涵。”
陈尧咨不禁疑惑的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去拿墙梯罢了,难不曾也算是是细作?”
贺山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道:“此与贺山来成都府,有莫大关系。”
范浱知晓他来历有些神秘,却是未曾问及,现在想来,却是不由得惊异道:“贺山,难不曾你真是党项潜入我大宋之细作?”
贺山面色一紧,摇了摇头,苦笑道:“我虽并非细作,却是来自党项无疑。”
“党项,”这秦小姐更是惊奇不已,“你自党项而来?”
贺山似是微微点了点头,抬起了头,看着陈尧咨道:“贺山虽有些好赌名头,乃是由西北之人所起。因而无人知晓贺山乃是党项之人,家父贺氏讳元,位在兴庆侍中之职,因受野利仁德之陷害,祸及满门,只有我一人逃离出来。本想在成都府避难余生,却不想昨夜借墙梯之时,被府衙之差役擒拿。”
陈尧咨不由得点了点头,道:“这位在侍中,乃是汉人之官职,想来你家在党项之时日,并不好过。”
贺山点了点头,却是又是一番沉思。
第25章 一线生机
范浱却是惊异无比,这贺山经历虽是看似奇异,却又不得不让人信服。没想这平日你嬉笑不已,似是无所忧虑的贺山,却又这么一番身世。
陈尧咨不禁奇道:“那你是如何到这锦官城的呢?”
贺山似是想了想,心中一丝苦涩之情,强笑道:“这锦官城,乃是我贺家祖籍所在,祖上孟蜀之时,迁至兴庆,世代栖居。在外游历的时日过久,便愿想着回乡。正是如此,才能得见少爷,贺山只感世事无常,世态炎凉,便想寻得一处地,苟全性命,了残此生罢了。”
几人听贺山娓娓道来,如奇闻所见,但看这贺山所言,也似是不曾有所欺瞒。陈亚强哦子不禁眉头紧蹙起来,从贺山所言,如今党项与大宋虽是正是盟会而拒吐蕃,可这奸细之事,必是突生波澜。贺山如真是党项细作,虽不免一条性命,这合盟之事必是有损。这贺山如不是奸细,岂不是枉杀性命,正中这章知州下怀,他必是乐见其成。
贺山见陈尧咨有所迟疑,不禁摇了摇头,道:“少爷,贺山命该如此,再也不要突生波折了,贺山死不足惜。”
陈尧咨暗自叹了叹气,道:“贺山,你可有何证据,洗脱你细作之嫌疑。”陈尧咨想了想,怕他不明所以,又是道:“即便是有可疑之处也可。”
贺山还是摇了摇头,沉声道:“贺山从兴庆入大宋,根本未通行大宋官府,也未入得土籍,便说是奸细也只能认命了。”
范浱听他如此之说,心中顿时又是焦急起来,紧紧地撰着他的囚衣,怒声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曾你自己也无法洗脱嫌疑。”
几人皆是一筹不展,秦小姐却是疑惑不已,柳眉微微而蹙,纤纤玉手不禁紧紧地撰着裙角,看了看陈尧咨几人,疑惑的道:“我大宋每年皆有外来之人,商贾游学者更是不可胜数,为何他们却是好好地?”
范浱也是点了点头,道:“如是贺山只是游学者,不是可洗脱细作之名了么?”
陈尧咨摇了摇头,道:“贺山一人之言,不能为呈堂供词。为今之计,便是找出其为细作之疑点。如是有疑点,便不可轻易定案,再徐徐图之。”
范浱不禁疑惑道:“这说的轻巧,要如何才可洗脱罪名,还是难以说清。”
陈尧咨不觉也是细细思索,便拉着范浱在角落细说了几句,范浱点了点头,急忙的去了。
秦小姐却是疑惑了起来,轻挑柳眉,道:“他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