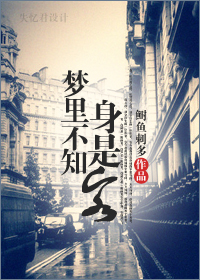梦里浮生之倾国作者:梦里浮生-第1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献约阂蛩绞路至艘坏阈模菔泵蝗ゴχ昧怂饨到棺砸徊蛔龆恍荩餍允赘孀约和寄辈还臁R篌ひ幌虺钟兄恍砦液θ耍恍砣撕ξ业男惺伦荚颍速鞅ǖ鞘贝笈骸胺戳怂耍∥乙姿还怨蕴簿桶樟耍垢腋嫖遥空媸腔钅辶耍 �
可是钱劲松作为重要首告人犯,业已被三法司带去候审,殷螭没到能公开提兵去攻陷内城的地步,想宰掉这活腻了的叛徒也力有未及。而钱劲松反叛或者说反正,仅仅是他手下将领纷纷自谋出路的明显化,袁百胜便失色向他秘密汇报:“末将该死,委实疏忽了!京营虽为末将所掌,却不料他们大多是赞同钱劲松领朝廷命离开的——钱劲松能去首告,即是京营故意监守不力,误了恩主大事!”
原来在殷螭图谋向内城羽林军浸润自家势力的时候,小皇帝也没有忘记向京营中进行反浸润。按理说小皇帝所拥的直属兵力除了主要负责保护内城与皇城的羽林军,便是分散在京畿各卫所的南京军,京师五营由袁百胜做主帅,应该属于殷螭的势力范畴,然而五营却又各有所统,刘秉忠全掌京营的时候,尚有很大一部分势力可以为他所指挥抵御外敌,不能听命于他反叛朝廷,何况袁百胜一个外来将领?此刻京营有刘氏的原部属,有京中旧派,有外调入京补充的力量,想法各别,属于袁百胜嫡系也就是殷螭死党的人手,并非营中全部。那些立场不属于殷螭一党的将士,服膺袁百胜的军事才能,却未必赞同他的政治投向,要京营共同发动政变,勒令小皇帝下台,比当年刘秉忠将殷螭骗到天津卫自家地盘上“兵谏”,有利条件实在是相差甚远。
所以面对这局势,殷螭不禁咬牙切齿,他虽然在床上跟林凤致说着什么都不想了,也真心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想了,可是一向做惯了搅事精,在他心里“见好就收”几乎等于吃亏,更加不肯白白送自己出去任人宰割。即使这等形势下也要腾挪的,立即指示袁百胜,将原本留在蓟州的大部秘密遣调回京师,又要想方设法将内城三门守兵换防,哪怕不能发动兵变,至少也要让朝廷不能轻易动自己。
但这种时候简直就是完全处于下风,继钱劲松首告之后,内城三门便全部换了兵马,不再是原来京营或倾向于袁百胜、或保持中立的势力控制,而是统统更换上最为忠心朝廷那的一拨人,袁百胜又不擅长于这些斗争,想要偷换上自己的人手都迟了一步,只能惶然跟殷螭请罪,殷螭反过来安慰他:“没事!我看钱劲松敢告我什么?我堂堂皇室嫡脉,好歹也陪京师守城四五个月,没功劳也有苦劳,安康那小鬼要是敢杀我,看他明君的招牌还打得出来!”
其实殷螭也知道自己就是侄儿的最大威胁,明君的招牌固然要紧,皇家的争斗却何时不是你死我活的血腥?区分只是做的漂亮不漂亮而已。当初殷螭急功近利杀害殇太子,便委实是失策之极,白白给自己留了老大把柄;而如今殷胍嘶龌迹比徊换岣冒壮盏氖迨逖埃欢ㄊ且右圆簧庵铮季莸赖赂叻澹运车母愕舨攀歉删弧�
所以钱劲松的首告,说的竟不是“靖王阻拦小将出城,意图加害,违背朝廷”之类伤不到殷螭根本的小事,直接告发一件大事:“围城之际,靖王实与外敌通谋。那刺杀徐尚书的奸细案,靖王便脱不了嫌疑——当初顺天府接报,称时太保窝藏刺客,以至靖王带兵抢人,与刘太师冲突,险些酿成内乱,实则即是靖王故意所为!”
当初时钧入大理寺受审,最终也没有审查出结果,便以年老多病为由取保候审,后来围城紧急,这桩无头公案便也搁置下来,却不料钱劲松忽然翻出旧案,登时将殷螭放到了极其不利的地方。
如今大理寺早换过新寺卿,身历四朝的铁面老臣汤宾仁早在清和六年致仕还乡,接手的官员远不及他有断案之才,遇上疑案便即哀叹棘手,而这回疑案牵涉到亲王,更加头疼,又要维持着三法司的架子,不能一旦不明头绪就推给皇帝亲断,于是只好硬着头发发帖公文去外城请教殷螭。称是“请教”而不直接提审,当然还是顾及到天潢贵胄的面子,殷螭却压根儿不加理会,直接无视:“笑话,从前只有我将人送大理寺的份,哪有自己被送进去的份?还想审我,也不掂掂他们斤两!”
其实所谓“从前”,也即是永建朝大理寺审理的最著名案件,不消说就是林凤致的妖书案,殷螭为这一案简直悔断了肠子,一是自己一败涂地,埋伏下群臣离心离德废黜自己的根由;二是那一场将林凤致也伤得不轻,险些天年不永,直到现在他一生病,殷螭便直接想到是被重刑拷打之后体质虚弱的恶果,一面骂着活该也一面难受不已——所以当年让林凤致在大理寺受审,乃是殷螭自认所犯最糊涂的错误之始,如今换到自己,是万万不能现世报应,也去挨大理寺特产小板子的!
好在到底他贵为亲王,又拥兵在外城驻扎,大理寺到底也没能耐强命他回复,更别提审理刑讯了。然而纵使被告缺席,案子还是要查的,继续调查之下,殷螭的罪名只有越加越多,连跟随他去敌营的护卫都被提审了,并且是该亲兵秘密潜入内城,紧接着钱劲松的首告,又告了一状更厉害的:“靖王在敌营在做人质之际,曾与敌酋铁儿努歃血为盟,约为内应,要学石敬塘故事,出卖国朝基业。”
殷螭在敌营跟对方随口应允合作的事,本来只有孙万年秘密告知林凤致,林凤致没替他往外宣扬,却私下里严厉斥责过,殷螭那时还觉得他小题大做,怎么能把敷衍话都当真?到这时被人告密,这才知道林凤致说的到底有道理:无论如何,外事交往上要懂得说该说的话,端该端的架子,轻率应诺,纵使自己全无半点诚意,也会成为政治上致命的破绽——殷螭一贯说话不算数,这回没兑现的话却偏要被人拿来算数,所以也算自食其果。
其实以殷螭所余不多的良心来发誓,当日暗杀工部尚书徐照的那批刺客,委实乃是蛮族所派,并非殷螭串通,但自己趁这个机会把嫌疑引到时钧身上——料想刘氏与时家有争斗,刘秉忠多半要上当去严查,自己便正好为岳父出头之名闹出内乱,大搅混水——这等勾当却一毫不错是殷螭的小诡计。那一回事态走向没有按照自己的谋划来,殷螭便根本不当作是自己的劣迹,被翻将出来还颇有委屈感,却不幸连带敌营中所作所为一起被告发,于是板上钉钉,将奸细与卖国贼的大帽子牢牢戴定,想申辩清白都不容易。
这两桩案子一出,朝中大臣自然群情激奋起来,纷纷上疏要求皇朝不可轻赦贼臣,尤其靖王这般包藏祸心,险些断送国祚,又怎么能姑息?继续推溯上去,就连当初击破山海关带兵直逼京城,蹂躏几处州县百姓死于内战兵火,也是殷螭与俞汝成联手干的罪行,更别提北寇便是他们引来,给国朝造成这一场重大灾难!俞汝成已死,孙万年降敌后又因心向国朝惨遭杀害,无从追究责任,却怎么能放过殷螭这罪魁祸首之一?
还有朝鲜归来的天朝平倭军,尤其是原属于高子则的部将,也联合上疏重新翻出朝鲜同室操戈之案,平壤一战,高军死伤不轻,这笔自家人的血债难道可以放过?何况殷螭不但与俞汝成联手,还几次同倭人使者接头,多半除了卖国给蛮族之外,还有卖国给倭人之心,这样为一己之欲闹得生灵涂炭、不惜卖国叛家之辈,有什么资格恢复封爵位列宗室?国朝刑赏如若这般不明,又怎么能励臣民爱国守土之心,示天下忠义仁爱之道?
所以殷螭这一来可谓是受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待遇,比较之下,以前群臣不时攻击他有不轨之心的弹劾简直就是无关痛痒的小玩闹。并且猛烈攻击他这些罪行,要求朝廷严惩的大臣们,除了一贯和他过不去的官员们,竟也有在围城之际向他示好、受他拉拢,提出“靖王监国”之说的那派人物——大约正因为曾经墙头草倒向殷螭,所以如今为了洗白自己,愈加态度严苛要与靖王不共戴天,反咬得比清议君子更为激烈。因此殷螭气急败坏的时候,居然会想到林凤致转述孙万年临别时的一句话,自己也不免感叹一下:“‘功高不赏,恩重不报’,原来真是至理——早知道我学老俞什么都干出来好了!”
可是“功高不赏,恩重不报”这八个字,委实应该由林凤致来感叹才是道理,因为林凤致的用心比他纯正,遭遇却并不比他好到哪儿去——殷螭的罪行一桩桩被翻出来的时候,他作为殷螭在朝鲜劫持利用的首领、归朝与叛党谈判的奉命者、同意和谈送靖王为质的主事大臣……无不沾染着重重嫌疑,尤其最后一条,连礼部都出来作证,当初本已将林凤致的名字填为质子人选,却是他亲自来改了名单,到底送靖王入敌营,去与敌酋勾结盟誓。这般情形,若说没有私弊,谁人能信?
殷螭在外城拥兵,群臣攻击虽然猛烈,朝廷不来动手也威胁不到,但林凤致属于无兵权的的文臣,沾上叛逆嫌疑,直接便可以褫夺衣冠送入大理寺去刑讯。而殷螭怕朝廷借机扣押加害,自钱劲松首告起便不敢离营落单,更别说再象以前一样只身入内城去找林凤致了,所以听到这消息,担忧起来,简直想索性攻城进去将他抢回来,逼他同自己造反——反正他终于也被拖下水了,难道宁可下狱,也不跟自己同生共死?
但内城三门换防,明显便是防范兵变,又兼法司审案、大臣攻讦的同时,军中也发生一次巨变——原本因为刘秉忠长子刘槲下落不明,导致无适合人选可以掌管京营,只能由袁百胜暂摄主帅,因此殷螭也能让袁百胜推辞朝廷调他去辽东的任命,留在京城为自己的臂膀。可是就在殷螭罪行被声讨得越来越激烈之际,城外卫所忽然送失踪的刘槲回京,据说刘少将军是因为在乱军之中受了重伤,幸亏被当地极少数未曾逃难的乡民所救,因当时京畿满布铁骑,难民只能躲入山野,直到世道完全太平,才敢出来谋生活。刘槲受伤甚重,亲随也尽数死难,还是乡民用推车将他一路推到最近的卫所,又报上朝廷送返。
按殷螭的想法,这等巧遇简直离奇如说书,就算刘槲侥幸大难不死,京畿也不是深山老林,怎么会拖延到今日才返京,正好掐准自己落败的时机回来抢兵权?所以其中必然有朝廷的掐算,说不定是小皇帝率南京军返京的时候,就埋伏了棋子算计自己!
可是刘槲带兵的才能虽然不及袁百胜,却也是跟随父亲多年,也算壮年将领中数一数二的人才,尤其是勇猛过人,当初他中夜突袭,连俞汝成都曾经吃过他的大亏,更何况他是刘氏嫡系,又协同父亲掌京营已久,这一回来,军中谁不期待?袁百胜再有才能,对于京营一部分老将领来说,也是属于“外人”,在人情关系上,争不过刘槲的。
就在刘槲自东面朝阳门被送返京城的当日,朝廷终于对连日以来大理寺的逆案调查报告,与大臣乱哄哄要求严惩卖国贼的呼声,由小皇帝亲自下诏作出了总结,称靖王乃朕之亲叔,围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