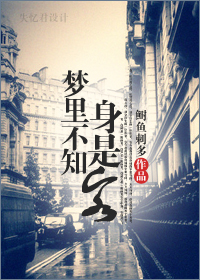梦里浮生之倾国作者:梦里浮生-第1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闭偬怠绷址镏潞鹊溃骸氨嘎恚〔挥么蚪危∥蚁热コ锹タ纯矗 蹦鞘孔涞溃骸把┨螅徽疽徽敬矗笕伺率强床患模√等娑荚诟婕保┏恰┏峭炅耍 �
中夜之间,这报讯的声音尖锐颤抖,充满惊恐,林凤致出来急了,未披斗篷,听了这不祥的话语也不禁一个寒颤。殷螭自后面赶来,拿着裘衣替他披上身,同时厉声呵斥:“什么完了?尽说丧气话!还没打到眼前就妖言惑众,仔细军法处置!”
他的厉害斥责将士卒给当场镇住了,但这样的丧气话却又如何压制得住?林凤致骑在马上飞驰向城楼的时候,原本沉睡在大年夜之中的京城,业已大半惊醒过来,到处都传着同样一句话:“关隘破了,蛮族来了,京城……完了!”
风凛凛,雪茫茫,即使登上了城楼,极目望去,到处也是一片黑暗,要在军中特训的守兵指点之下,才能勉强望见三面隐约有着红焰闪动,是自长城关隘一站接一站的直传过来,向京城紧急示警。林凤致的目力望不穿这长夜的黑,刺不破这漫天的网,只觉满空雪片扑天盖地的砸落,无处遮护脚下城池。
三之29
作者有话要说:过场戏……不好写也不好看,擦汗。 伴随着清和九年元旦第一缕曙光而来的,乃是长城关隘被北寇击破的噩耗,而且惊人的是:这回被击破的却既不是一直在苦苦捱持的居庸关,也不是一直受到骚扰不敢放松的密云关,而是京城根本不曾放在心上的山海关——东面这座关隘正是俞殷联军来袭的突破口,进入关内后,仍然留业已归降殷螭的原守将王可安把关,并且还留下一部分精兵协守,保证俞殷二军的退路不失。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朝廷固然对这座雄关有失防范,连殷螭也觉得那里是根本不会有失的,却不料首先被破的,竟是决计想不到的这一处要隘。
理由却实是简单:王可安能被殷螭游说反水,那么也就能够被俞汝成暗中策动,于是也就未尝不会出卖国朝利益给外族。何况在如今南北分裂的局势下,在京师无援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自保也罢,想趁乱分一杯羹也罢,应形势而生的想头,都会成为滋生野心、促使变节的大好缘由。
京城并非不曾面临过长城被破、兵临城下的危急处境,前几回被破的还是直隶、山西的关口,铁骑倏忽便长驱直入,这回首先被破的山海关却挨在渤海边,敌军纵使直线过来也要好几日工夫,京中本不该如此慌乱。但分裂、无援、离心,这座城池在被困之前已经充满了孤危不安之感,何况铁骑已入,很快就要抵达城下来围困?林凤致冒着大雪从城楼赶入宫中的时候,所听闻的便是一片悲凉哀鸣,连兵部尚书章守成都是脸色灰白,请罪之余,连声催促太后立即率六宫起驾赶往天津卫,到海上去躲避,不然万一京城有个闪失,宫眷蒙辱,岂非连国朝体面都没有了?
刘后到底已经历过一回围城,当此时竟是比大臣们都镇定,在垂帘之后声音沉着:“清和四年情势更紧,哀家都不曾离去,这时又何必走?难道先生们要哀家弃了京城?”章守成急道:“太后贞义可风,臣等不胜景仰!然眼下迁宫,并非弃城,也决计不是南下,只是暂请鸾驾移于海上,免受惊恐……”刘后道:“海路也是风波不定,惊恐到处都要受的——哀家反正是未亡之人,走与不走都是一样,太傅以为如何?”
林凤致正从殿外入来,首先便是厉声驳斥章守成:“章大人此言差矣!如今已是人心涣散,若是迁宫,一发不可收拾!”户部尚书杜燮自免税提案通过之后与林凤致一派颇是结了嫌隙,但这时却赞同起林太傅的言语来,也坚决反对迁宫避难:“太后所言甚是,清和四年难道不是比眼下更为紧急?那时连陛下都在京中,也未迁出,终究有惊无险!想我圣朝列代陵寝之所,赫赫英灵保佑……”章守成道:“四年那回,最终赖得各路勤王军来援,京城才终究固守未失,如今……”
如今这情势指望勤王军来援,只怕难之极矣,因为北寇南下多日,各地如若有意救援,早在关隘血战之际便来了,迟迟不来,足见各地守军都在观望,要看南北两京最终谁是正主。这个时候最能盼望的,反而是南京方面出师来援——从南到北自然不是那么容易过来,真正赶到只怕也远水不解近渴,但南京若是出师,便是摆明态度,就近的勤王军才敢出动,京城才有捱持下去的信心。
然而南北两京分裂如此,互相攻击如此,小皇帝亦是情况不明,未知他还能掌到几分权力,还能否压服南京朝臣?正如林凤致在刘后面前说过的,迁都派认为定都南京有无数好处,惟独不好的一件就是弃北京于外族,所以南京朝廷将迁都变成事实的时候,未必还顾念这块土地。
因此,后宫万万不能弃走——南京群臣或许不在乎这里的土地与百姓,更不会乐意来救把他们骂作乱臣贼子的北京官员,但太后见在,宗庙见在,皇陵见在,小皇帝到底持有道德的利器,用以压服、遏制、与周旋,只要他还能稳住阵脚,别再大出昏招,愈想掌握主动权却愈是背道而驰!
决不迁宫,其实未必不是正如南京群臣所斥骂的那样,以太后等人为质,劫持朝廷守住京城——或者说,以太后等人为赌注,赌一个保全与胜利的可能。
首辅叶德明也不赞成后宫迁向海上躲避,但对于林凤致等人这样狠决的主张,却还是不免心惊胆战的,退出宫门时禁不住一声长叹:“公等……莫不是要做寇莱公?”林凤致正色道:“国家只患无寇准,何计其他?”
北宋寇准封莱国公,在辽兵大举南侵时力排众议,阻止宋真宗南迁西幸避难,并劝说其渡河亲征,终于结成“澶渊之盟”,然而胜利后却被奸臣攻击,说他不许皇帝避难而力劝亲征,乃是拿君王来做孤注一掷,博得自己忠义护国之美名。这样的谮害正打中越想越后怕的皇帝心里,于是寇准到底遭到贬谪。此刻林凤致等人坚决反对太后迁宫,绝对也逃不了“孤注一掷”的评语,叶德明这持重老臣不觉心有栗栗。
不仅是文臣中有人建议太后立即迁宫避难,就连武将也持同样看法,当日下午刘秉忠便亲至宫门,奏请太后移驾天津卫暂避。刘后已经坚定了主张,命人出来直接拒绝:“若是将军都不能坚信守住京城,百姓复有何恃?迁宫之言,休再提起!”
然而就算后宫坚守不移,百姓的惊恐不安却哪能尽消?自山海关西来的铁骑还在路上,京城中已是哭喊一片,南下逃难的平民更加增多,就连官员中有些极没骨气的,也开始偷偷化装成百姓,携妻带子潜逃出城。京中一面急调守兵向西扼守,一面镇抚城中不使动乱,连续动荡了两日之后,又来一个噩耗:继山海关被破之后,居庸关也终于失守。
居庸关在延庆卫所,乃是京师西北面的大门,北寇南下便来叩关,将士已接连抵御了近一个月,仗着关隘牢固,火炮精准,尚能捱持。但两京分裂的局势,已是暗自削弱军心,待得闻知山海关已破,军中情绪一乱,登时支持不住。
这一来北寇竟是东西两面同时破关,犹如一把钳子夹向京城。况且山海关距离京师还远,居庸关急驰过来却是日内便至,所以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京中又是一番剧烈的沸腾。刘秉忠已将京营增派向靠近京城的卫所,只待短兵相接,谁知北寇自居庸关下来却没有直抵京城西北门,两三日之后,却有大量南逃的难民纷纷涌回北京城来。
原来京畿一带,尤其是西北一带的居民已经遭受过两回北寇蹂躏,这一回早在听说关外血战之际,各县镇的居民都已入京与南逃,跑了个干干净净。蛮族原以抢掠为主,先锋部队入了居庸关之后只遭遇了白羊口所抵抗,然后便一路势如破竹的冲杀下来,岂料各地十室九空,毫无子女财帛可抢,如何不大失所望?铁儿努的主力大军尚在外面,先锋的铁骑便勇往直前的向南杀至,竟然暂时绕开京城,至石景山、渡卢沟桥,反来包抄京城南门逃出的难民。平民哪有铁骑的速度,平原上也无处奔逃,只好又回过头来投奔京城躲避。
南城一带正是殷螭的驻扎地,南城门也算是殷军参与管理着,但难民纷涌而来的时候,九门提督却来急传军令:“左安、右安、永定三门,全部关闭,不得放人进城!”
这一来涌到南城之下的难民登时恳求哭骂声响成一片,得到急报的兵部尚书章守成立即去问刘秉忠为何不放难民入城,刘秉忠只是一句话掷将出来:“京中奸细尚未拿获,倘若难民中再混匪徒,谁来负责!”
这句话使京中军民大为愤慨,因为难民中不无他们的亲戚眷属,何况敌军未至,先拒百姓,这样的做法如何服得人心?于是以林凤致为首的文官们亲自出面调停,连殷螭也派人出了个折中方案:“既怕难民混有匪徒奸细,大不了放将入来,先关押在南城便是——我军愿意负责看管,只是兵力嫌少,请求调拨骁骑营相助。”
这个主意听起来居然大是不错,虽然包括林凤致在内的官员,都知道殷螭才没有那么善心大发救助百姓,只是一来要博好名声,二来正好趁势扩充势力,于是乐得逆刘氏而动。刘秉忠前日还在指责他的降将王可安卖关投敌,难保这前废帝不是勾引北寇潜伏京城的最大祸根,被殷螭又一阵撒泼反咬抵赖了过去,正气得倒仰,如今又在接纳难民的问题上被他将了一军,偏生专门掣肘的文官们还怂恿了太后亲自降诏同意,刘秉忠虽然有跋扈之名,却难以公然抗命,只得忿忿解禁,南面三门齐开,难民们连日直涌入来。
如此一来,殷螭在市民中的口碑又好了几分,再加上他自己不遗余力的鼓吹,使得“靖王监国”的请求,在民间与官场又愈发响亮起来。须得内阁大臣拼命压制,才不使其成为事实。
但殷螭想谋取增兵的主意却不曾实现,并未获得京中调动骁骑营归属自己调拨,他所驻的“南城”其实乃是京师的外城,与内皇城隔着一道深垣,外城的居民人数远比内城稀疏,还有大片荒地。殷螭驻在天坛之东,接纳了难民也暂时关押在附近营帐里,没几日难民越增越多,驻军处吵嚷不堪,他手下的精骑军也渐渐人手不足,于是大叹失策,成天跑去跟林凤致等一干文臣诉苦不休,坚决要增兵,不然不干了。
所以林凤致一面应付殷螭以公事为名的骚扰,一面防范他以公谋私的揩油算计,还要尽力调停刘秉忠与文官间越来越深的嫌隙,连日也是烦恼不堪。到正月十二,东面山海关过来的蛮族骑兵正在步步深入,对南逃百姓追杀抢掠了一番的铁骑也调转头来攻向京城时,刘秉忠一直嚷着京中有奸细的猜测,终于得到了一个坏证实——十二日夜间,工部尚书徐照遇刺。
徐照以精通格致之学、擅长研发火器出名,一直便是蛮族盯牢的目标,自清和四年蛮族吃过火器的苦头之后,屡屡派人来窃取机密而未遂,其间也曾经想过绑架或者除去徐照。但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