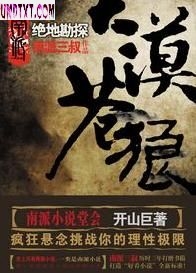[悬疑]大漠苍狼2-绝密飞行-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一刻我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就在昨天,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和难题,等着那个敌特来闯,我能想象他当时的纠结,但是现在,他把所有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还给我了,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几乎和他一模一样。
如果他躲在里面,手里有一把匕首,只要我进去就立即会被伏击,但是,我不进去,没发离开,
。
这里的木板十分的结实,没有王四川的铁棍,我也灭有办法把出口弄大,爬进去几乎等于送死,心中的郁闷别提了。
犹豫了半天,只有冒险试,赌里面一片漆黑。
我把拿下来的木板和几个背包都背到胸口,心里拿着三角铁,用双臂撑着,面朝上爬了进去,一进去我用左手挡在自己面前,几乎是贴地蹦着,几乎感觉有人扑了上来。
然而等我爬进去翻身站起来,谁也没有扑上来,我静下来戒备,感觉里面非常安静。
愣了一下,我小心翼翼地打起手电,找了一圈,里面什么人都没有,而一边的墙壁上方,有一个被拆掉的通风管道口。
我有转了一圈,确定没有人,一下子觉得好笑,妈的,完全是自己吓自己。
把袁喜乐叫了进来,我看到她熟练地踩着床铺上去,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也跟了上去。
通风管道还是同样的构造,但显然不是我们来时候的那一条,我们一路往前爬,很快前面出现了出口。
从另一头的通风管道口子出来,我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手电往四周处一照,就意识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水池的上方。
整个房间都是锈得生起鳞片的铁壁,没被水浸没的地方有六七米高,至于水下有多深不知道,一水池的死水全部都被铁锈染成了以一种浑浊的红棕色。
我用手电扫了一圈,发现四周水面以上的的铁壁上,有无数的通风管道出口,而从通风管道的口子出来,有一条走廊贴着铁壁围了这个房间一圈,绕着走廊可以通过说有的通风管道道口。
看来这个地方时整个通风系统的空气净化室,大量的空气在这里交换进化。
另一边的走廊上有一道门,袁喜乐非常开心地跑过去,拉了一下,门好像被锁住了。她的面色一变,显然有点不敢相信,又拉了一下,我帮她去拉,发现门被卡死了。
我用力敲一下门,这肯定是那敌特干的,他娘的他除了锁门还会干什么。
手电照向其他的通风管道口,我不知道这些管道能不能通道其他地方,立即拿出了平面图,去看这里的结构。
可惜,平面图上没有我想要的,这种隐秘的设置会被利用作为渗透和偷袭的通道,所以标有通风管道的平面图肯定是保密的地图。
不过走运的是,我在图上看到了这个房间的位置,我发现,在这滩死水的下面,有一个通道通道外面的地下河里,距离大概有五十米,不算远,问题是,在这个通道的出口上,有铁闸门用来换水,必须打开它才能出去。
这个闸门的开关,就在当时司令部隔壁的那个控制室里,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到那边,但是,我有了找电缆的经验。
闸门的电话不会太复杂,而且,电缆尽量不会在水下走。
所有的通风管道里都有电缆,这里也同时是一个电缆的枢纽,我找着找着,很快找到了一条通道水里去的唯一的电缆。
我脱掉自己的外衣,包着三角铁,把电缆的皮刮掉,然后找了其他差不多粗细的可能通电的电缆,把两条电缆一接,火光四射,地下的污水开始出现漩涡。
这是首先的排水过程,这水脏成这样,我也不敢跳下去。很快水酒换清了,我和袁喜乐对视了一眼,我抱着她一下跳进了水里。
手电入水后坚持了几秒就灭了,但已经足够我看清水下通道的方向,我们摸黑游了进去。
五十米的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我不知道袁喜乐水性如何,也不敢大意,只管往前游,一边游一边随时摸自己的上头,看是不是游出了管道。
然而大概是太紧张了还是什么缘故,我一路游下去,很快觉得气紧,儿摸着上面,一路都是管道的顶部。
我不由得着急起来,想着是不是先回去看看平面图,如果看错了,等下一点气也没有了,那岂非要活活淹死在这里。
犹豫的时候,手脚慢了,而气也更加急了起来,胸口开始发辣,我很想吸气,知道自己一定得回去,否则很可能呛水。
刚想拉着袁喜乐返回,她却推着我不让我回去,我肺的气这时已经完全净了,被她推了几下,完全慌了。
慌乱间她拉着我的手,用力捏着,然后示意我往前,非常坚决。
我下意思地跟着她,几乎是在极限中坚持了几秒,忽然头顶摸空了,可以上浮了。
意识半游离中,我一阵目眩,发现有无数的灯照向了我,我觉得莫名其妙,被人抓住了手,拉出了浮筒。
二十章 生变
另一边的袁喜乐也被拉了出来,我被地下河上的冷风一吹,人缓了过来,吃惊地发现四周全是工程兵,另一边,到处都是大型汽灯把整个基地照得通亮,在河道上,我看到了大量的皮筏上全是运着物资的工程兵,足足有几百人。
“怎么回事?”我摇摇晃晃地说,还没有说完,那些扶着我们的人分开,一个军官从后面走了过来,对我敬礼,让我们跟他走。
我被他们扶着,一路走在铁网道上,看到很多设备被防水帆布盖着,都是在地面看到的那些,现在竟然全部运了下来,而近处,无数的人在解构这里的设施,一直走到一处物资以后,我看见一个军官站在了那里。
我认识这个人,看到他出现在这里,我立刻意识到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人姓程,不是工程兵部我们系统里的,但我在克拉玛依见过他。他是跟随地质队的正规部队总指挥,负责一切周保卫和保密事务。
我们都叫他程师长,他的部队番号很是有名的华西军区二十四师,只要是当年去过大西北靠近新疆的人,都会知道这支部队,他出现在这里,让我非常意外。
在克拉玛依,他对我们非常客气,但是这个人能看得出平时不苟言笑,是个职业军人。
看到我们,立即走了过来,看到我没力气说话,对扶着我的人道:“送到医疗队,我马上过来。”
边上的人立即拖动我们,我们被送到帐篷里,我看到了之前在陆地上碰到的医务官。医护人员看到我们都迎了上来。
我此时还拉着袁喜乐的手,她必须要去另一个帐篷,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也不想放手,但是一个女护士过来拉她,我看着四周的人,忽然犹豫了一下,手一松,瞬间她已经被人不认拉开。
她没有反抗,只是看着我,我抬了抬手,想说我就在她隔壁的帐篷,让她别害怕,但她已经被簇拥着进了一个医疗帐篷。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当时有了一种错觉,忽然,在我们之间出现了一层奇怪的东西,让我觉得非常不安,但我没能够多想,就已经看不到她了。
我也被送进了另外一个帐篷,我就问他们怎么回事,怎么大部队全部下来了,一声以为深长地看了看,让我别问那么多,该我们知道的,我们都会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休息。
我的衣服被换下,开始做身体检查,我看着沉默的医护人员,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起来。无论发生了什么,大部队下来了,背后一定有重大的原因。
可惜,这样的不安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我躺下之后,被遗忘的疲惫好像潮水一样涌来,在护士为我输液的过程里,我慢慢睡了过去,真正地睡了过去。
我一个梦也没有做完,完全失去了知觉。
再醒过来,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身体,一定在两天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折磨,身上各种酸痛无法形容,简直连脚趾甲都觉得酸痛。医生还不让我下床,只吩咐护士给我吃一些流食,然后继续休息。
我问他袁喜乐怎么样了;他就朝我暧昧地笑笑,说和我差不多,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那种笑让我很不安。我几次想溜出去看看,但是使不上力气,总是下床就躺倒在地上,后来护士就对我发脾气说,每次摔倒一次都会让她被批评,我再摔倒她就要被记处分了,让我老老实实在床上躺着。
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怎么了,我对自己有一个判断,知道绝对不会躺几天就站不起来,心中开始不安,心说该不是中毒的后遗症?
后来问医生,医生告诉我,这的确是副作用,但不是因为中毒,而是用了解毒剂的原因,那种毒气对人的神经系统有影响,这几日我挂的吊瓶里都是解毒剂。
我心中奇怪,难道他们已经知道我中的什么毒了?但是再问,医生却没有透露更多,只说等我伤好了,在详细和我解释,因为这种毒气的运作机理很复杂。
那个年代阶级观念很浓,该不该知道,该知道多少都是很明确的,我也没有为难他,只问什么时候可以下床走动。
他说最起码还要三天时间,之后看尿检的状况,这种毒气对我身体的伤害性是永久的,我本身吸入得不算多,可能不会再年轻的时候体现出来,但老了之后会很麻烦现在处理得好不好,对以后的身体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我想袁喜乐应该和我是一样的情况,甚至她应该比我更严重,不由得担心起来,但这时没有力气,我总不能趴着去见她,于是只好克制住自己。
三天后,我果然被准许出了帐篷,被人搀扶着,只能在帐篷外的凳子上坐了一会儿。但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发现整个基地已经灯火通明,短短几天里架起了大量照明,以及无数的帐篷。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感觉到一股不对劲。
这么多的照明设备和这么多的人,看来大部队会在这里驻扎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没有等我们返回就全部下到洞里来了,这显然表示上头的计划有变。难道我们在洞里的时候,上面发生了什么,所以让他们这么大动干戈。
二十一章 一切都只是开始
虽然医生和护士对于当时的事情都讳莫如深,但从其他人对话的这种蛛丝马迹中我感觉到,上头的决定下到洞穴的原因本身就十分的晦涩,他们也许不明白自己做出这样的举动的原因。
唯一明确的,就是这些人被通知准备出发的时间,就在老猫进洞两天后。
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们和老猫困在仓库里的时间。
从日本人当时绘制的整条地下河的分岔图来看,我们所在的勘探线路应该是最重要的,不过,确实也有其他支流也会汇聚到“零号川”。
我觉得能够解释的是,也许探索地下河分支的其他勘探部队已经有人回归了,并且带回了非常关键的东西,使得上头作出了更改计划的决定。
至于是什么东西,我完全无法判断。事实上,我觉得即使是我们带出的胶片,也没法使得上头决定下来这么多人,如果确实像我想的那样,那其他分队带上来的东西,一定让上头觉得了,下来长期驻扎是值得的,并且是必要的。
从我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东西也许本身并不重要,比如说上头感兴趣的,也许是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必须低温冷藏的炮弹。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在病床上的臆想,真正的原因,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知道,这我倒不在乎,我不能知道的事情,在当时多了去了,也不差这么一件。不管怎么说大部队的出现,终归是一件救命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