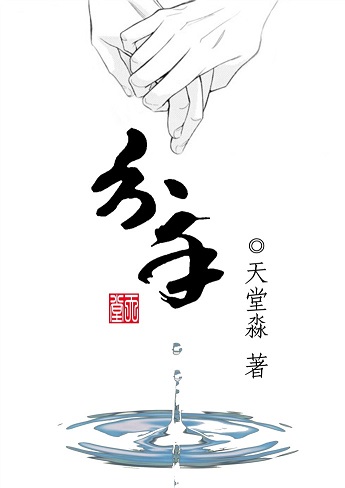分手美学以及其它艺术-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被吵得慌:“回家吗?”
“回家。”卫来搂过了我。
午夜的街头,是安静的梦境,夜游的人成为肆无忌惮的神,卫来尤其肆意。“池旻攸,我们试试吧。”
“试什么?”我脚步发虚,思维跟不上现实。“恋爱吗?”
“恋爱,吵架,厌倦,沟通,再恋爱,始终在一起。”卫来揽过了我的腰。“我想试试两个人的生活。”
“我不想试。”
“为什么?因为闫岑忻?你——”
“跟他没有关系,是我个人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非要这么刨根问底吗?”
“有疑问当然要找到答案。”
“我不尝试。所有的实验都带有不确定性,失败的总是多数——”
“你是这么看待爱情的?”
“我这么看待绝大多数事情。”我以为爱情在绝大多数之外。只是我的妄想。
“池旻攸——”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不是你的画,或者作品。我一点儿也不温暖。我不想变成疯子,让我正常到死好吗?”让我正常。我已经过了无知无畏的年纪,任何风吹草动都是我的教训。
“旻攸。”
“我累了,跟你说话让我觉得累,就到这儿吧。”所有的,到此为止——
“那么明天见。”卫来并不放弃。
他每天都会去探望外婆,职业迎合喜好,外婆喜欢艺术多过商业,这是她欣赏卫来多过闫岑忻的根本原因,而我的感情丝毫不计算在内。“把窗户打开,我透不过气。”外婆说着,转头对卫来道:“我有些话想单独跟旻攸讲。”
卫来随即起身,对我轻笑:“我在门外等你。”
“他追求到你了?”外婆的问题,毫无疑问的奚落。
“总之不是您想的那样。”
“你知道我想成什么样了吗?”外婆冷笑。“过来。”我听话的过去,跪在她的床前。“抬起头。”外婆倾过了身,我越发不敢看她。“什么时候学会顶嘴了?”
“我错了——”
“这句话我听厌了,再不想听了。旻攸,我折磨了你小半辈子,你也折磨了我,我们俩互不相欠。”外婆递给我一张纸。“这是你父亲现在的住址。”
“父亲?”我没明白——
“你父亲没死。他这么一个胆小的人怎么会舍得自己死,你就跟他一样——丑陋,愚蠢,胆小如鼠。我女儿看上的男人,简直是个废物,你该庆幸时代不一样了,更多的人包容你这样的废物!我恨你父亲!”
“外婆——”
“不要再来了,我已经跟你无话可说了。”
“外婆——”
“不要叫我外婆。”
“您恨我,对吗?”
“我恨你。明明是我女儿的孩子,却丝毫没有像她的地方!旻攸,知道我对着你有多痛苦吗?恨不得跟你同归于尽!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你是我孩子的血脉!是我的血脉!”外婆喘不过气,抓着胸口,“滚”字就在嘴边,横竖落不了地。
立夏过了,云压得低,梅雨的尾巴憋得人发闷,我跪在外婆的床前,算着她的呼吸,渐渐地,没有呼吸。她没有骗我,至始至终都没有骗我,她恨我,我却想让她骗骗我。“外婆。”我轻言,不再害怕外婆。她死了,手里的纸条字迹模糊,是汗。一身冷汗。
作者有话要说:
☆、第 30 章
我不知道医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跟我说了什么,他们又跟我说了什么,外婆睡在那儿,平静又安详。“旻攸!”卫来摇醒了我。“你还好吗?”
“好?好——好啊。我不是孤儿,我还有个父亲,你知道吗?我是有亲人的。”我无法正确表达情绪。撞击在胸口间的情绪,五味杂陈。“我有——”
“你有我。”卫来抱紧了我。
可我如何拥有你?一个海市蜃楼的未来。“外婆死了,我看着她咽气的,我不想救她,她说过她会死的,她不想让我救她。她恨我,想报复我,她让我去找父亲。她在报复我。”我恨她,不亚于爱。外婆是我唯一的亲人。
“没人能伤害你。”卫来亲吻我。点滴的吻,轻柔,全是安慰。“我在你身边——”
“没有人在我身边,没人能伤害我。”没有人,才不会有伤害。
死因报告是心衰。因为发现的时候已经断气,医生只是形式上的做了急救,没人责问我的疏失,卫来替我遮掩了一切。我依旧是那个池旻攸,孝顺寡言木讷到令人忽略。葬礼定在三天后,需要通知的人不多,我连流程都梳理不好——“有黑西装吗?你只要老实穿好衣服就行,其它的我来做。”卫来跟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确认了各种细节。我盯着外婆的遗照发呆。“难受吗?如果想哭——”
“我哭不出来。”为什么要为恨我的人哭泣。她是基于仇恨才抚养我的,她纵容了我的软弱。
“旻攸——”
“我一直在等这一天,我以为死亡能让她对我好一些。可惜,感情跟死亡无关。”我想得到的,统统都离我远去。我不敢问外婆究竟有多恨我,我怕我会恨我自己。
“我送你回去!”卫来把我塞到车里,锁死了车门。
我懒得反抗。沿途的风景都与心境无关,生命的荒凉才衬托世俗的繁华,我还得生活,还得活着。“有烟吗?”我的烟抽光了。
卫来腾出一只手,扔给我半包烟:“迟早有一天你会得肺癌死掉的。”
“迟早。”我认为这是好死法。至少死在自己的爱好里。“喂,你不害怕吗?”
“什么?”卫来笃眉,打转方向。我跟他透过后视镜观察彼此,折射了视线不折射态度。
“我杀死了外婆——”
“你并没有杀死她。”
“本来她还有救——”
“你只是没有救她。”
“有区别吗?”
“客观上来说,我得庆幸你没有犯罪,至于犯罪的思想,那是人的主观自由,你可以在脑子里谋杀她无数遍。”卫来的冷静,冷过了英俊。“就像我想象着在不同的场景里强。奸你。”
“你——”我只能讪笑。卫来总有本事让我的罪恶感合理化。“强。奸!”
“强。奸比做。爱有戏剧性,想象比行为更具有扩展空间,你是我的灵感。我很期待看你穿黑西装的样子。”
“只是一个葬礼——”
“葬礼过后你的外婆就于你无关了,还想陷在她的阴影里吗?”卫来的问题,比语气锋利。
“你根本就不清楚我经历过什么——”
“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清楚另一个人经历过什么,经历只是思想一部分,我愿意接受你所有的想法,好的坏的都可以,不够吗?”
“不知道。”我整理不了我的思想。
车停在小区前。“明早我来接你。”卫来比我有条理。
“其实你不必这样——”
“是不是必要由我来决定,你只需要心安理得的接受我的帮助就可以了,我不讨论我们,那是之后的事情。只希望到那时你不要逃避。”
我想要逃避,无处可去。我站在日头下,看着卫来的车远去,似乎要下雨了,空气里都是水分,这场雨过后就是盛夏了吧?很难让人消沉的季节,消沉无比。
“抱歉,我不能出席葬礼。”柏康昱靠在A座门口,真诚道歉。
“没关系。”我理解柏康昱的焦虑。死亡总是令人沮丧。
“嗯,那个,我叫了外卖,要一起吃吗?”她有些犹豫,宽慰显得孩子气。
“好啊。”我欣然接受。外卖,还有拙劣的身同感受。
柏康昱把附近尚可的店的外卖都叫了。“我想选择多一些会好一点儿,我不知道你想吃什么,鱼生还是牛排,或者鸡汤,我不知道,我——”她哽了,好一会儿才找回声气。“我没有经历过朋友亲人的葬礼,我,我紧张了。”
“没什么值得紧张的。”我抱过了柏康昱。我让我的老少女紧张了,紧张到自闭,却努力克服恐惧关心我。
“她是你外婆,虽然我不喜欢她,我——”柏康昱踮着脚,圈住了我的颈项。“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我就是不喜欢她,可她是你的——该死!我不晓得该说什么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在这儿,在我身边就行了。我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在你身边。”柏康昱抱紧了我。
“身边”如此具体,又如此疏离,我们根本就靠不进彼此,徜徉在各自的安全距离里,扮演彼此的依靠,她撒了谎,我热爱这个谎言。我们坐在一堆食物的面前,忏悔食欲,忏悔以前。柏康昱说她是因为我们的名字有一个字很像才跟我做朋友的,我不相信。她大叫“是真的!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我才开始认真对待肤浅的深刻。
“你就没想过或者没有认识我比较好?”柏康昱从冰箱拿出一瓶剩一半的汽酒。
“为什么?”我不喝酒,明天还得参加葬礼。假装置身事外,仅仅是参加。
“如果你没有认识我,就不会认识闫岑忻——”
“我不后悔认识闫岑忻。”
“真的?可他是个混蛋——”
“除了出轨那次,他无可挑剔。我跟他的问题远不止郁璟,我们都在逃避,他只是选择了不聪明的方式结束,即便他不想结束——”
“就算你这么帮他说话,我也不会改变想法!他是百分百的混蛋!边飒是百分之一千的混蛋——”
“你后悔认识边飒了?”后悔绕回后悔,我从不辜负选择。闫岑忻珍惜过我,我一直珍惜他。
柏康昱闷掉一口酒。“不后悔。”
“所以啊——”
“所以啊!我不仅肤浅,还很白痴!问了个这么白痴的问题!”柏康昱喝光了汽酒。空的酒瓶存放一颗心。
“白痴。”
白痴枕着我的腿,她说她可以睡着了,问我怎么办:“——你的失眠症比我还严重。”
“那就不睡,等到天明。”不过是一晚,算不上折磨,没有香烟才让我惴惴不安。半夜,柏康昱似梦非醒的问我想不想闫岑忻,我没有回答。
晨曦初起,卫来打来电话:“我现在从工作室出发来接你,准备一下。”
我把柏康昱抱回卧室,回了B座,洗澡刮胡子换衣服去超市买烟,刚好看到卫来的车过来。“要吃东西吗?”我顺便买了三明治和咖啡。
卫来打开咖啡,两口喝了光:“走吧。”
“或者我来开车?”
“怎么?”
“你熬夜了——”
“你没有?”
“我睡不着才正常。”
“好吧,你来开车。”卫来把钥匙抛给了我。
车开到了殡仪馆,可准备的事情并不多。外婆的朋友很少,我还认不全,只得任由他们挑剔。闫岑忻来了,全然亲眷礼数。“你该通知我的。”他这样说。
“岑忻——”
闫岑忻并不理会我的难堪,对卫来道:“你不介意吧?”
“没什么好介意的。”卫来递给闫岑忻一块孝牌。
怪异的场面,身份失误,在别人的眼里,闫岑忻和卫来都是外婆的外孙,我成了最不起眼的一个。也许,外婆满意这种局面,我只能这样想。棺材推进火炉的那一霎,我摘掉了孝牌,戏落幕了。我用尽半生演的戏,不知值不值得回票价。
“你去哪儿?”闫岑忻问我。
“去律师楼听遗嘱。”我点了根烟,现实却不随烟雾蒸发。
“我送你——”
“我送旻攸!”卫来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