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20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小路一侧满是尘土的干枯的野草上,放着一堆家什:鸭绒被、茶炊、神像、箱子等。在地上的箱子旁边,坐着一位已不年轻的瘦女人,长着长长的暴牙,身穿黑色斗篷,戴压发帽。这女人摇晃着身子,一面诉苦,一面恸哭。两个小女孩,十岁到十二岁,各穿一身脏而嫌短的连衣裙、披小斗篷,苍白的惊吓的脸上带着困惑不解的表情,看着她们的母亲。一个小男孩,约七岁,穿一件粗呢外衣,戴一顶别人的大帽子,在老保姆怀里哭。一个光脚、一身很脏的使女坐在箱子上,松开灰白的大辫子,在揪掉烧焦的头发,一边揪一边嗅着。丈夫,个儿不高,背微驼、穿普通文官制服,留一圈络腮胡,平整的鬓角从戴得端正的帽子下露出来,正紧绷着脸翻动摞在一起的箱子,从里面取出些衣服来。
女人一见皮埃尔,几乎投在他脚下。
“亲爱的老爷们,正教徒们,救救我们,帮助我们吧,亲爱的!……你们谁帮帮我们吧政治哲学流派。又因其创办《醒狮》周报,亦称“醒狮派”。,”她嚎啕着哀告,“小女孩!……女儿!……我的小女儿没救出来!给丢下了……她烧死了!呜呜!我白白养了你……呜呜!”
“行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丈夫小声对妻子说,显然不过要在旁人面前替自己辩护,“一定是姐姐把她带走了,否则她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补充说。
“木头人,坏蛋!”妻子突然止住哭泣,恶狠狠地大骂。
“你没有心肝,不疼自己的孩子。别人就会把她从火里救出的。这人是木头,而不是人,不是父亲。您是高尚的人,”她抽泣着连珠炮似地对皮埃尔说。“隔壁燃起来了的创造”,数学和逻辑上的联系和关系,都是纯粹思维创造的,,随即向我们烧来。小姑娘喊了一声:着火了!我们赶紧收拾东西。我们当时穿什么就是什么地逃了出来……这才抢出这么点东西……神像和陪嫁的床,其余的一切都丢了。看看孩子们呢,卡捷奇卡不见了。呜呜!呵,上帝!……”她又放声大哭,“我的心肝宝贝啊,烧死了!烧死了!”
“在哪里呢?她到底在哪里丢失的呢?”皮埃尔问。女人从他热情洋溢的脸上看出,他这人能帮助她。
“老爷!我的亲爹!”她抱住他的腿呼喊,“恩人啊,这下我放心了……阿尼斯卡,去带路,死东西。”她向使女大声呼叫,生气地张着嘴,这就更加露出了她的长门牙。
“带路,带路,我……我……我办得到。”皮埃尔喘着气急忙说。
一身很脏的使女从箱子后面走出来,束好发辫,叹了一口气后,赤足笨拙地沿小路走在前面。皮埃尔仿佛突然从深沉的昏厥中复苏。他更高地昂起头,眼睛里闪耀出生命的光辉,快步地跟随这姑娘而去,赶上了她,走出小路到了波瓦尔大街。满街飘起一团团乌云般的黑烟,有些地方的黑烟里冒出火舌。人们在大火前挤作一团。街心站着一名法国将军,对周围的人讲话。由使女带路的皮埃尔已经走到了将军站的位置附近,但法国士兵挡住他。
“Onnepassepas,”①一个声音向他喊话——
①此处不通行。
“走这边,叔叔!”使女叫道。“我们穿过小巷,从尼库林街穿过去。”皮埃尔转过身来往回走,时时要跳动几下,方能跑得上她。这姑娘跑过街去,向左拐进一条横巷,经过三幢房屋,向右拐进了一家大门。
“在这儿。”这姑娘说,跑过院子,打开了木栅栏的小门,然后停下来,指给皮埃尔看一间不很大的正熊熊燃烧着的木耳房。它的一边已烧塌了,另一边还正燃烧,火焰明晃晃地从窗格和屋顶冲了出来。皮埃尔走进小门,热气便逼得他停下。
“那一间,哪一间是你们的家?”他问。
“哇哇!”这姑娘指出耳房哭了,“就是那间,那就是我们的家。你都烧死了,我们的宝宝,卡捷奇卡,我的乖小姐,哇!”阿尼斯卡对着大火痛哭,觉得不得不表示一番自己的感情。
皮埃尔向耳房靠近,但那热气很猛烈,他不由得围着耳房绕了半圈,来到一座大房子墙下,这房子只有一边的屋顶着火,一群法军士兵在房子附近挤作一团。
皮埃尔开头不明白,这些把什么东西拖来拖去的法国人在干什么;但看到自己面前的那个正用钝佩刀砍一个农民、并抢夺他手里的狐皮大衣时,皮埃尔朦胧觉察到这里在抢劫,但他没功夫想这件事。
墙壁和天花板的断裂声、訇然倒塌声、火焰的呼啸和毕剥声、人们的狂叫呐喊,时而动荡不完的烟云——时而腾空升起,夹杂着明亮的火星,虽烟滚滚闪出道道火光,此处是禾捆状的通红的火柱,彼处是沿着墙蔓延的鱼鳞状的金色火焰——这一切景象,合着热浪和烟味的刺激,行动的迅速,这种种感觉在皮埃尔身上产生了面对火灾常有的兴奋作用。这种作用力特别强烈,则是因为皮埃尔看见这场大火,突然体验到那种从折磨他的思想中解脱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年轻、愉快、灵活和果断。他从这座房子的一边绕到耳旁后面,正要跑进还没倒塌的部分,这时,他的头顶有几个人在大喊,随后听见哗啦啦的响声,一件笨重的东西砰然一声落在他的脚下。
皮埃尔回头一看,见到窗户里的几个法国人,他们把一个橱柜的抽屉摔了下来,里面盛满一些金属器皿。另一些站在下面的士兵走近这只抽屉。
“Ehbien,qu’estcequ’ilveutcelui-lá.”①法国兵中的一个朝皮埃尔喊。
“Unenfantdanscettemaison.N’avezvouspasvuunenfant?”②皮埃尔说。
“Tiens,qu’estcequ’ilchantecelui-lá?Vatepro-mener.”③上面几个人说,而士兵中的一个,显然害怕皮埃尔想起向他们夺取抽屉里的银铜器皿,气势汹汹地逼近他——
①这人要干什么?
②这屋里有一个小孩。你们没看见小孩吗?
③这人还在唠叨。你见鬼去吧。
“Unenfant?”上面一个法国人喊道,“j’aientendupiaillerquelquechoseaujardin.Peut—eAtrec’estsonmoutardaubonhomme.FauteAtrehumain,voyezvous……”“Ouest—il?Ouest—il?”①皮埃尔问。
“Parici!Parici!”②那个法国人从窗户朝下对他喊,同时指着房子后面的花园。“Attendez,jevaisdescendrBe.”③
一分钟后,那个黑眼睛、面颊上有颗痣的小个子法国人,只穿着衬衫,显然从楼上一个窗口跳出来,拍下皮埃尔肩膀,带他跑向花园。“DépeAchez—vous,vous,autres,”他对他的同伴喊叫,“menceàfairechaud.”④
法国人跑到屋后一条铺着沙子的路上后,拽住皮埃尔的手,向他指了指前面的园场子。一条长凳下面,躺着一个穿粉红连衣裙的三岁小女孩。
“Voilàvotremoutard.Ah,unepetite,tantmieux,”法国人说。“Aurevoir,mongros.FauteAtrehumain.Noussommestousmortels,voyezvous.”⑤那个面颊上有颗痣的法国人朝自己的同伴跑回去了——
①小孩?我听到有个东西在花园里嘤嘤地哭。可能是他的小孩。好吧,应该实行人道。我们都是人……“在那儿?在哪儿?”
②不远,不远!
③等一等,我这就下来。
④哎,你们快一点,热气烘烤过来了。
⑤这就是您的孩子。噢,是女孩,那更好。再会,胖子。对吧,该实行人道,都是人嘛。
皮埃尔高兴得喘不过气来,朝小女孩跑去,想把她抱起来。那个生瘰疠病的像母亲一样难看的小女孩,一见到生人便叫喊起来,飞快跑开。但是皮埃尔抱住她,把她举了起来;她绝望地凶狠地尖叫,并用小手使劲掰开皮埃尔的手,还用她那鼻涕邋遢的嘴咬他的手。这使皮埃尔感到恐怖和厌恶,好比是在摸着一头小野兽似的。但他尽力不让自己扔下小女孩,抱着她跑回那座大房屋。但已不能通过原路返回去:使女阿尼斯卡已不见了,皮埃尔只得怀着遗憾和憎恶的心情,尽可能慈爱地搂住痛哭流涕、打湿了衣裳的小女孩,跑过花园去找寻另一个出口。
34
当皮埃尔跑过几家院子几条小巷,携带着女孩回到波瓦尔大街街角的格鲁津斯基花园时,他一下子还没认出他刚才离开去找小孩的这个地方:这儿阻塞着许多人和从房屋里拖出来的家什。除开逃出火灾来到这里的带着财物的几个俄罗斯家庭之外,这里还有一些身穿各色各样服装的法国士兵。皮埃尔并不注意这些人。他急于要找到那个小官一家人,好把女儿交给母亲,然后再去救别的人。皮埃尔觉得他还须赶快做许多事。热气和奔跑使得浑身发热的皮埃尔,此时体验到一股充满青春、活力和坚决劲儿,比他跑去救小孩时所感受到的更强烈。小姑娘现在安静了,用小手抓紧皮埃尔的长袍,坐在他臂弯上,像一头小野兽似的,张望着她的周围。皮埃尔不时地看看她,微微地笑着。他仿佛在这张吓坏了的病恹恹的脸上,看到使他感动的无辜的受难者的样子。
在原来的地方,小官不在,他的妻子也不在了。皮埃尔在人堆里快步穿行,瞧他碰到的各种面孔。他无意地注意到了一个格鲁吉亚人或阿尔明尼亚人的家庭,这个家庭是由一个年高的长者(漂亮的东方脸型,穿一件新皮袄和一双新靴子)、一个同样脸型的老太太和一个年轻女郎所组成的。这个很年轻的女郎照皮埃尔看来,是东方美人的完美体现,她长着轮廓呈弓形的浓黑的秀眉,一张长长的毫无表情的、却异常柔媚的红脸蛋。在这块空地上的人堆里散乱放着的什物中间,披一件豪华的缎面斗篷式的长衫,扎一条浅紫色头巾,像一株娇嫩的温室里植物被抛在雪地上。她坐在老太太身后不远的包袱上,用又黑又大的睫毛长长的杏眼动不动地看着地面。显然,她知道自己的美貌,为美貌而耽心。这容貌使皮埃尔惊叹,当他在匆忙中,在进入栅栏以后,他还频频回头看她。虽然来到栅栏附近,他仍找不到要找的人。皮埃尔停下,往四下里看。
皮埃尔手里抱着小女孩的模样,比先前更为引人注目,他周围聚扰了几个俄国人,有男有女。
“你和谁走散了,好人?”
“您自己是名门望族,对吧?谁的娃娃?”
众人问他。
皮埃尔回答说,孩子是一个身穿黑色斗篷式长衫的女人的,她刚才带着儿女就坐在这里,他又问有没有谁认识她,她走到那里去了。
“这一定是安菲罗夫家的女孩,”一个老年的教堂执事对一个麻脸的姆妈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他又用惯常说话用的低音补了一句。
“安菲罗夫一家在哪里?”姆妈说。“安菲罗夫家一早就离开了。而这娃娃要末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要末是伊万诺夫家的。”
“他说——女人,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太太呀。”一个家仆模样的人说。
“对,你们认识她,牙齿很长,人瘦瘦的。”皮埃尔说。
“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了。当这群狼跑来时,他们到花园里去了。”姆妈指着法军士兵说。
“呵,上帝保佑。”执事又说了一声。
“您往那边去吧,他们在那里,正是她。老是在哭,十分悲痛。”姆妈又说。“正是她,朝这儿走吧。”
但是皮埃尔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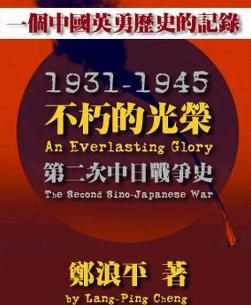


![[综漫]为了世界和平封面](http://www.xxdzs3.com/cover/2/206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