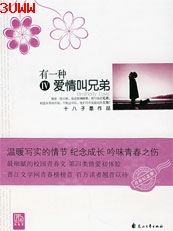哪一种爱不疼-第9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院,有一里多路必须步行。他说他是六点出发的。
他看到她时,俊眸倏地晶亮。不过十多个小时没见,但今日意义是不同的。
苏晓岑和叶一州在柠都宾馆摆了十六桌,说祝酒词时,叶一州眼眶红了。
吃完饭,下午,叶家和苏家的亲戚就坐包机回青台了。
苏晓岑想到把叶枫丢在这人迹稀疏的山林,觉得自己象个狠心的后妈,很没形像的抱着叶枫放声痛哭。
“妈,我和奕阳从海南回青台时,你去机场接我们好不好?”叶枫乖巧地替她拭泪。夏奕阳说山里面实在太冷了,两人只呆三天,然后去海南度蜜月。
“每天都要给妈妈打两通电话,至少。”苏晓岑抽泣着。
叶枫重重点头。
烟花、礼鞭在安岳县城的上空一遍遍回荡、绽放,叶一州牵着叶枫的手放进夏奕阳的掌心,礼花象雪片一样落下,四周响起掌声和笑声。
“爸爸、妈妈,我们会好好的。”夏奕阳郑重地承诺。
他拥抱叶一州和苏晓岑,与所有的亲戚寒喧,亲吻每一个孩子的脸腮。当他的视线最后落到叶枫身上时,那种热度瞬间温暖了四周。
叶枫还是觉得冷,不住地搓手、搓脸,脚冻得象块冰似的。
山路非常颠簸,她被弹得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夏奕阳只得不顾伴郎们的取笑,将她抱在怀中。山里天气黑得早,走了不到几十里,本来就浅浅的日头就不见了,往上一看,黑压压的大山,车象山中的一块移动的岩石。
“你以前上学都是这样走的吗?”叶枫问道。
夏奕阳笑而不答。
“说呀!”叶枫推他。
“山里通汽车是最近几年的事,以前有时是骑自行车,有时搭人家摩托车,有时步行。”
她听得心一紧。
盈月和老公在村头都快站成两棵歪脖子村了,终于看到汽车雪亮的光束,盈月欢喜地忙跑过去,让老公着人准备放爆竹。
“嫂子,路上还好吗?”
叶枫哆嗦地扶正花环,点点头。她不好意思说她严重怀疑她浑身的骨头都被颠得散了架,以至于她走路时脚步有点怪怪的。
所谓村子并不是一家挨着一家,又没路灯,深一脚浅一脚,走好一会才看到一盏灯火。倒是空气清新得很,鼻息间都是山林独有的草木香气。
黑夜里突然升起一串火光,劈哩啪拉的响声,把叶枫吓了一跳。
“叶枫,咱们到了。”夏奕阳轻轻地说。
叶枫抬眼看去,心想全村差不多都出动了吧!夏家只有三间的平房连着一个院子,根本容不下多少人,不得不在院外搭了个大大的帐篷来容纳热情的宾客。
她不想承认自己是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但是众人投过来的目光,显然把她等同于那珍贵的国宝。
她听到许多人都发出一个象感叹样的语气词,盈月告诉她,“嫂子,都夸你漂亮呢!我还对他们说了,我家嫂子出过国,会说洋文,主持节目、拍广告,有本事着呢!”
她扭头寻找夏奕阳,真正有本事的是那个人,诱惑得她不问东西南北,傻傻地随着他转。
夏妈妈自豪地领着叶枫去见亲戚们,她听不懂方言,夏妈妈让她叫人,她就模拟夏妈妈的发音叫一下,挺有原汁原味的。最后是来到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面前,夏妈妈看看地,笑眯眯说了一句什么,她也看看夏妈妈,跟着重复了下。
哗地一下,围观她的人全笑了,有的还笑出了眼泪。
她纳闷地看着众人。
“傻丫头!”夏奕阳走过来,宠溺地笑道,“妈妈是说这是我家媳妇。”
她闹了个大红脸,不过,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天气太冷了,她冻僵的面容,笑,是硬挤起来的。
人群纷纷象潮水般退开。
有一个憨憨的小伙子,一手拿了把菜刀,一手抓了只嘎嘎叫个不停的大红鸡公,突地一抬臂,刀落向鸡公,鲜红的鸡血围着她洒了一圈。
“嫂子别怕,这叫撵煞!”盈月看她慌乱地依向夏奕阳,手搭成喇叭叫道,“意思是你和哥以后的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安安全全。”
“嗯嗯,谢谢!”她瞪大了眼睛,不知下面将发生什么。
堂屋大门坎上挂上了一条红布,“这是跨红,以后咱们家因为你,会兴旺发达、和和美美。”夏奕阳柔声在她耳边说。
“必须的。”她迈开大步跨了过去,与夏奕阳在佛案前双双欠身。
爆竹声把山林都吵醒了。所有的仪式结束,酒席正式开始。因为没有大灶和液化气什么的,所有的菜都是火塘慢慢烧出来的,菜上得极慢,十多桌转一圈,最后一桌吃到的菜都冷了。
但这丝毫不妨碍婚礼的喜庆。叶枫都没机会碰到筷子,就被夏奕阳带出去敬酒、发糖、递烟。
虽然她的位置是在堂屋的正中,但是她再次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冻成院中的一根冰雕了。
这种锦缎棉袄,只是薄薄的一层棉呀,她在里面穿了两件羊绒衫,还是挡不住从山里灌进来的寒风。
零下十二度的冬夜呀,她真的想让夏奕阳找件大衣让她加上,可是……她不能让客人们失望。
新娘,应该是最美的,在今夜。
在去厨房向做菜的师傅和相帮的亲友送糖时,她陡地发现厨房实在是个好去处。在火塘边烧火的婶婶热得只穿了一件棉毛内衣。她握着婶婶的手,凑到火塘口,幸福得都想哭了。
于是在外面敬酒时,只要夏奕阳和别人用家乡话寒喧时间长一点,头一转,叶枫就不见了。
烧火的婶婶骄傲地对烧菜师傅说:“新娘子和我最投缘,爱和我拉家常。”
“叶枫,当心火苗碰到衣服。”夏奕阳从火塘口拉起叶枫,忍着笑,人家新娘脸上有红有白,她的脸上却抹了层黑灰。
“不会,我很小心的。奕阳,我好冷。”朝外面探了个头,她忍不住说出了口。
“冷吗?不会吧!”夏奕阳已经把大衣给脱了,鼻尖上还有一层细细密密的汗。
难道她是个怪胎?她看看四周,就连坐在帐篷里的客人,四周没有任何遮挡,确实没一个人象她这样冷得缩手缩脚的。
“干杯!”她听到酒杯碰击的激荡声,巡睃着喧哗的酒桌。
她明白了。
再敬酒时,照例是夏奕阳喝酒,她递烟。这次,发完一圈烟,她端起了酒杯。“各位不要计较了,她一碰就会醉,我代她喝。”夏奕阳象起哄的客人歉意地打着招呼,回身欲接她的酒杯。
“这是我的酒。”她紧紧地攥住。
夏奕阳挑挑眉。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醉又何妨?”她眉宇飞扬。主要是酒精可以让血液沸腾,能从脚趾温暖到心脏。
她一仰头,喝尽了杯中的酒。众人拍手,连夸新娘子爽气。
夏奕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酒席一直持续到凌晨,宾客才逐一散去。叶枫温婉地坐在椅中,闹新房的那帮人和她说话,她都是呵呵一笑,不发一个词。
“嫂子是不是醉了?”盈月悄声问夏奕阳。
夏奕阳瞟了眼叶枫,笑了笑。“没事的!你去给我拿两瓶开水。”他给众人又是发烟又是赔礼,把人打发走了。这才走过去,一伸手,叶枫柔顺地扑进他的怀中,笑得更甜了。
盈月应了声,先去看了下俊俊。俊俊撑不住,已经在外婆的床上睡着了。她出来和老公还有妈妈说了几句话,这才从厨房提了两只水瓶走进新房。
门是掩着的,她推开,脸一红。夏奕阳正在给叶枫脱衣服,叶枫就象个孩子,咯咯地笑着并不配合。
“乖啦!”夏奕阳轻哄道,任由她揉乱了自己的头发。
“老公,老公,你……是我老公!”叶枫此时真的是娇艳如花,轻抚着他的嘴唇。
“哥,我先出去啦!”盈月识趣地准备带门。
“呕……”门还没关紧,她戛地又推开,只见叶枫的身上、夏奕阳的前襟全部沾满了叶枫的呕吐物。
“傻站着干吗?快来帮忙。”夏奕阳叫道。
叶枫现在真的是乖了,说脱衣就举臂,让净口就张开嘴巴,幸好婚床没有沾到。红烛摇曳,熏香轻燃,夏奕阳长舒一口气,掀开锦被,将叶枫搂进怀中。
盈月在离开时,很不厚道地对他说:“哥,你这个洞房花烛夜真是很特别啊!”她偷偷给夏奕阳把酒换成了水,不然,这新房里够闹腾的了。
叶枫睡得很沉,鼾声也比平时重,滚烫的肌肤象个小暖炉熨贴着他的胸膛。
是有一点小遗憾,没有让洞房名副其实。“老婆,你该怎么弥补我呢?”他轻吻着她的脖颈,哑声轻喃。
醒来对,只觉屋子里特别的亮堂,一时不能适应,他又闭了下眼,才睁开,发觉怀里的人蜷着身子已经坐起了。
他正要说话,叶枫朝他竖起手指,“嘘,不要说话,听雪落的声音。”
雪,一般是不声不响的,但在寂静的山野的清晨,屏气凝神,可以听到簌簌的轻声。
“下雪啦!冷不冷?”他也坐起。
她点头,将身子埋入他的怀抱,“冷,床也硬,外面安静得过分,我很早就醒了。”
他有些心疼,“后天我们就去海南了,那边非常暖和。”
“这样的环境我没呆过,只是不适应,我会让自己努力去接受的。”
“一大早讲这么令人感动的话,是想弥补昨晚的失误?”他调侃道。
她坐正,自上而下地打量他,“如果是呢?”
四目相望,空气中立时有了暧昧的味道。
“我……很期待。”喉结急促地蠕动。
她微笑地仰视他,雪光里、晨光中,清丽的眸子中,闪过一星火光。她翻身跨坐上他的身子,双手搭住他的双肩,用力一拽,他整个人被拉得更贴近她,不等他做出回应,叶枫顺势就吻上了他的唇。
“犯错的人是我,所以我甘愿伏法……”
他心里对这绮丽的一幕有所准备,然后回吻她时仍然激动得有些不能自已。他的手颤动地解去她的上衣,一只手握上她胸前的饱满,轻轻地揉捏。
她加重一点力道啃咬他的肌肤,手轻如羽毛,俏皮地,沿着他结实的腰线慢慢向下,突地,瞬刻抓住了他的灼热,引领着他慢慢地进入她。
填满的那一刻,他和她不约而同都呻吟出声。
她从来没有这样取悦过他,他被她带入幸福的顶端,闭上眼,彩虹满天,直至汗湿颊背,他揽紧气喘吁吁的她,吻住她的嘤咛,两人双双躺下,身体靠得更紧密。
“喜欢吗?”她用手掌去磨蹭他有点刺刺的胡渣。
“我不介意每天都来一次。”
“贪心!”
“这是我应得的福利。”他温柔地笑着。“起来吧,我带你去爬山。”
她穿着他中学时的旧棉袄,裹得象只狗熊,千难万苦地爬上夏家院后的山顶,俯瞰着下面小小的村落,雪花纷纷扬扬打白了她的双肩,他指着山林,说他儿时的趣事。
她觉得,她的婚礼虽然没有婚纱,没有鲜花、礼堂、结婚进行曲,甚至都没有用摄影机拍下来留作纪念,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她回想起这一切,仍会情不自禁地欢笑。
因为,珍贵的回忆,不是刻在光碟里,不是写在纸中,而是烙在心底。
番外3…专利
海南是暖的。
糖果一样浓甜的花朵,放肆地从空中开到水里,天蓝得让人心里发空,太阳亮得让人觉得整个人都在慢慢融化。
在机场脱了大衣和棉袄,路上又迫不及待地脱掉毛衣。虽然有许多人组团来海南过冬,酒店没有想像中那么紧张。
尽管两人都戴了墨镜、帽子,搞得象地下工作者似的,登记时总台小姐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