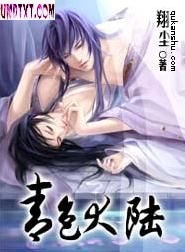青色平原-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天后,当绪东往小铁床上铺被褥时,主顾上门了,一个汉子走进来探头探脑,四处看着,问:“你这儿有没有三联的防疫药水?我家一窝猪该打疫苗了。”就这样,一九九零年春寒料峭的一个下午,绪东的事业不动声色地开张了。
晚上,绪东躺在暖和的被窝里,枕着手看着雪白的顶棚,闻着淡淡的清冷的油漆气味,心里也和那顶棚一样,白净亮堂。
第二天上午,又有个半大小孩子用草筐带一条小狼狗来,叫绪东看,绪东诊断是缺钙,开给他一瓶钙片;又有个中年人来买猪用泻盐;又有个老太太跟绪东说,她家一群母鸡“不知遭了什么瘟,拉满院子青白痢”,绪东配了两样药粉给他。这些都不费功夫。他那屋子背阴,冷,没人来的时候就去大门外走一走,晒晒太阳。
门南旁管小店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朴讷少妇,样子很朴素,绪东听见买东西的人都叫她翠兰。她丈夫也是个寡言男子,送了一趟货来。门北首卫生室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半少老头,绪东早几天就知道他叫田明权——这庄上九成的人家都姓田——黄白清瘦,却是个极健谈的人,又极喜谈论国家大事,提起国际国内的大事情他没有不知道的,常滔滔不绝地一讲一两个小时,中央的时事评论员也没他风采。
今天,他屋里和往常一样,又聚了三五个和他一般年纪的时事通,就国际形势“发表了看法”,分析一阵,嘲骂一阵,有两个挣得脸红脖子粗,“制裁”与“反制裁”的呼喝声几乎掀翻屋盖,仿佛联合国就是他们家的。绪东在太阳地下听了一会儿,觉得很有趣——政治很无趣,这些人很有趣。
中午,他在二姑家吃了饭回来,见明喜正往大院里走,后头跟着个拉车的汉子,车上高高一堆花生秧儿。绪东赶上去帮他推了一把。明喜开了门,绪东问道:“上午怎么没来?”明喜道:“耕地去了,怎么,想我了?”绪东笑了笑,“你说呢?”明喜一笑,嘴巴更大了些。他开始穿戴工作服,绪东进屋东瞧西瞧。
屋子的墙壁非常粗糙,粘满了面粉草粉,毛茸茸的挂了羊毛壁毯一般。屋里两台机器,一台在里头用布盖着,这是打面粉的。外头一个宠大的家伙打饲料、草粉。墙壁上有一块木板,上头缀满了电闸、电表、电线头什么的。绪东是个不懂电的人,望而生畏,小心绕了过去,生怕碰一下就被电死了。
那汉子把草车堵上门,用草杈只顾往里挑。明喜把机器下料斗那儿拴的一条白布口袋理开,开了电闸,嗡!机器的轰鸣震耳欲聋,那条白布口袋得了神力似的,倏然挺开,饱涨滚圆,成了一条奇大无比的肥白肉虫,绪东用手指捺下去,软软的,非常肉感,感觉也是捺着了肉虫。
明喜把草只顾往机器里填,空中烟尘斗乱,群魔乱舞。绪东呆了一会儿受不住,逃出来一看,肩头上已薄薄落了一层灰。
一车草一会儿打完了,明喜落了电闸,那条肉虫仿佛着了巨人的一脚,登时塌了,明喜再把它肚子里的货抖出来,整个成了一层皮,面目回复成口袋,不再引起绪东肉虫联想。
然后过磅,付帐,汉子拉了两袋子草粉走了,绪东过去帮明喜掸掸灰,又去磅体重,明喜问:“多少?”绪东道:“一百三十五。”明喜笑道:“比我重一斤,不过你才吃了饭,论起来还没我重呢!”吊了水来洗了手,又提了一块破木板跟绪东说:“这是军刀。”绪东道:“知道知道,你是日本鬼子。”明喜故意凶着脸:“我是日本太君,怎么能叫日本鬼子?你地!八格!”破木板抡起来就劈,绪东抬脚一挡,劈到鞋底上,“军刀”裂成好几段。
“你日本太君又怎样?我是八路军,照样把你打回老家去!”
两人玩了一会儿,身上开始热剌剌起来。明喜解开了军袄的扣子,很认真地对绪东说:“我们田庄这地方最好了。你现在还不熟,熟了就知道!”绪东道:“有多好?有你那么好?”明喜笑了笑:“跟我一样好。”
他咧着大嘴,唇上透明的茸毛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像四月天青涩的桃。他年纪只比绪东小一岁,看起来却像小了三四岁。绪东是个出来做事的人,更成熟一点,而且,他天生似乎有些老相。这种人有个特点,就是年少时不显得年少,年老时也不容易显老的。他似乎一直就这么不老不嫩不丑不俊着,他看起来是个稳重从容的成年人,然而在他内心里的某些地方,仍旧和明喜一样,青涩得像四月的桃。
青郁迷离的田庄,此刻如同伊斯兰的女子蒙着黑纱,绪东早晚要掀起这层面纱来,走进她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天,即使是在许多年之后。
田庄村辖的三个自然村:豆腐坊、柳墩、小新庄,宛如田庄未成年的妹妹,再是伊斯兰的世界,也一目了然。田庄本身三个生产队却大,而且要复杂得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绪东知道有一处所在叫“圩里”,“版图”吃进了三个生产队的各一小部份,呈东西走向狭长的一条,早先有一人多高的圩墙,现在早坍塌得不落一点痕迹,然而它还是“圩里”。
如果说保国家这一段新排房是新村区的话,那圩里就是老村区,如同城里的老城区。新村区整齐划一的砖瓦排屋,房前屋后全是白杨树,是田庄连年扩张的结果。圩里却复杂得多,砖瓦房占绝大多数,也有草屋,草屋里住着城里人所称的空巢老人,另外就是些特贫困的人家。白杨很少,多的是杂树:桑、棠梨、合欢、臭椿、本槐、洋槐、紫穗槐、青桐、小橡树、小孩拳、榆、楮、……另外还有些没人叫得出名儿的乔木和灌木。桑叶可以养蚕,桑椹是孩子们初夏的好吃食;棠梨结一种褐色的小果实,能看不能吃;合欢只能看;香椿的嫩叶是可以吃的,香椿拌豆腐是春天的一道时鲜名菜;臭椿做新婚用的大床,取它一个“春”字的谐音;本槐的花蕾可以做黄色染料,每年初夏,有本槐的人家都使了孩子拧下花蕾来,晒干之后买给下乡收购的贩子,换几个油盐钱;洋槐花也可以吃,叶子又是兔子的好饲料;榆钱也可以吃,只是现在没什么人吃它了;紫穗槐取其枝质的柔韧,编制各种器物;橡树和小孩拳所结果实都是小孩子的玩具……
然而还有一样不可忽视的一样植物:臭橘子,就是“橘逾淮为枳”的枳。全株有一种怪味,果实似橘而小得多,味极苦,当地人叫臭橘子。秋天打下来也可以卖的,做药材。然而田庄的祖先们种这个似乎并不是为了卖臭橘子,而是有别的、更大的用途——防风帐子,防盗障子。
第2部分
这种植物全株墨绿色,多刺,少叶,叶是墨绿的蜡质。农历四月开白色的小花,却是很好看的一种花——世上不存在不好看的花——洁白而寂寥的花朵,是乡村的纯情女子,没有谁会在意。他们只在意它们的针刺。成排地种着,种得密密的,长大后针刺交锁,郁郁青青,密不透风,有两三米高,是极佳的防风墙。村上人都叫臭橘帐子。倒底是臭橘帐子还是臭橘障子?没人说得清。如果是防风的初衷,那该叫臭橘帐子,可是它似乎还有个防盗的用途。旧社会匪患猖獗,村上家家户户都种,连成排,成为一种生物的围墙,类古战场上的鹿寨。贼人钻吗?钻不过来;搭梯子呢?上是大约可以上得去,下来呢?密集的刺簇拥着,想下来是件相当棘手的事,不,是相当棘身的事。砍倒几株吗?下头砍倒了,上头却拉不出来,交织得比帆布还要紧密;全部砍倒吗?天!又是一道防御工事!
不管怎样,臭橘障子是大有用途的。但是现在少了许多,一是没人种了,二来开路建房建猪舍,嫌碍事,砍倒了,然而残余的仍有十之五六。要是再闹匪乱怎么办呢?绪东听说,田庄原来匪乱挺多的。
那是解放前的事,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这地方也是土匪横行,各自为乱,匪与民,匪与匪,混战不休。当地人都称为“贼”,有别于偷鸡贼的“贼”,也叫“马子”。田庄本庄就有几个,有叫“小皮袄”的——据说是因为抢了个皮袄而得此名——有个叫“烧包”——爱穿新鲜衣服,故称“烧包”。这“烧包”是个很横的贼,手下有百十条枪,一条枪就是一个人。他是个像样的贼了。后来让他一个徒弟打死了,从后头一枪崩了后脑勺。
那个叫“小皮袄”的,解放的时候在曹沟地方叫人捉住了,差一点被整个死。他们割下他屁股上的肉,塞到他嘴里叫他吃,还要问着他:“好不好吃?”他赞:“好吃!”他们把他开了膛,用木棒撑开肚皮,愤怒的人群往他肚膛里扔石子,扔了一肚子。后来拉回田庄来埋——他也有近房的——埋在村南的地里,许多年后耕地,还能耕出一种红皮石子来,本地没有而曹沟有的。那时死了多少贼呀!据说有一个是用棒子秸活活烧死的,烧得缩成黑黑的一团,孩子般大。有个女贼也死得很惨——是的,还有女贼呢!
一个叫……什么大娘,应该是个少妇,丈夫也是个贼,先被人打死了;她死的时候是个傍晚,刚吃了晚饭,被一个叫“老木耳”的村民用一根铁标枪捅进肚子里,晚饭都带出来了。又有一个叫“小洋盘”,为什么叫“小洋盘”?现在大约没人知道了,据说当初是被“烧包”抢来的,后来就做了贼,是个为虎作伥的伥鬼。老人说她生得白净标致,骑个大白马,英姿飒爽。她倒是没有死,解放后不知所终。
是的,那时候是乱世,乱世里有乱世佳人。田庄出乱世佳人,是个让人伤神的地方。现在是太平盛世,出什么佳人呢?太平公主?
绪东以后会见识到的——他会见识到的。
三、花开的早晨(1)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是清明——一九九三年的清明,绪东已在田庄过了三个清明节——又是纷纷的雨。已下了好几天了,下得人百无聊赖,闲得心里发慌。
绪东也很闲,一连几天几乎都没什么事。他望着铅灰色的正在潇潇落雨的天,他知道,不久他就会忙起来的,凭他做兽医这几年的经验。
阴雨天很少有人打面,明喜也不来了。绪东闲着只好出大门找人说话。同那个朴讷的翠兰当然没什么话讲,有买东西的人聚一会儿闲聊,他就去聊一阵,人一走,他也就走了。大多时候是去卫生室找田明权说话。明权也很喜欢他去,他发表政治评论有了听众了嘛,他当然很来劲。
他脱了鞋子,蹲踞在高高的高脚凳上,俨然一只大公鸡,居高临下地对着他的唯一听众。他谈起中国人民的朋友苏联的解体,毛头小子美国倒长成个世界警察。他对苏联有深厚的感情,他谈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斯大林;然后不自禁扯到莫斯科保卫战,希特勒……接连不断地扯起根山芋藤似的,他顺着那根藤说个没完没了,一个个极具份量的人名和地名从他嘴里不断地蹦出来:巴顿将军、诺曼底、易北河……在崎岖破损的卫生室水泥地面上一砸一个坑。他不断地挥舞着双手,仿佛扯着面正义的大旗;唾沫星子飞溅,迸射到绪东的脸上,绪东仿佛看见二战战场上的连天炮火,横飞血肉……
绪东低了头,局促不安,头发里不痒,也忍不住想挠挠头皮。他是个“读书声不入耳,天下事不关心”的人,他只知道做好自己的本职——兽医,他只关心牲畜的病因和治疗方法。为此他感到自卑,觉得自己是个全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