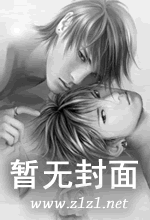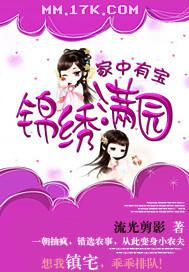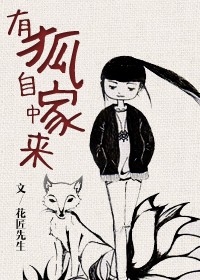家中养猪的副团长之死-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巴斯”在哈萨克族语中是最受尊敬的人的意思。虽然他才49岁,可所有认识他的职工群众和下级,无论长幼,都亲切地叫他“郭巴斯”和“老郭”。大伙儿说,这样叫他亲切,郭斌也喜欢大家这样叫顺耳。他的骨子里,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官”。
得知郭副团长走了,二连老职工郭云华伤心地说,还不如让我这样的人替他走啊!
在二连职工群众眼里,那座简易的水厂在他们心中大得像一片天。
二连的生产生活条件曾经是全团最差的。每年夏天,职工群众饮用的是从庄稼地里流经过的含有化肥、农药等物质的“涝坝水”。由于水质问题,连队各种疾病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职工住的全是“干打垒”的危旧住房。
“再让老百姓这样过下去,我们心里不得安宁呐。”通过郭斌向团党委建议,投资40多万元的二连改水工程和危旧住房改造工程全面实施,他亲自带领工程人员逐项落实。
眼看整个工程就完工了。11月3日,郭斌亲自带着铲车来给二连的职工平整住宅区,一直到中午两点还没吃饭。职工郭云华连着请了两次,郭副团长也不愿去打扰,自己让人买来白菜炒粉条和馒头,就凑合过去了。
职工群众都知道,郭副团长从来不愿给职工群众添麻烦,到基层检查工作,他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对老百姓有益的事,郭斌一点儿不含糊。一次,郭斌在检查一条道路施工质量时,发现有一小块没达到质量标准,他十分少见地向在场施工的负责人发了火:“你敢糊弄我?糊弄得了老百姓的眼睛吗?团党委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最终,这条道路高质量地完成了。
二连饮水工程和危旧住房改造工程的实施,使连队职工群众彻底告别了吃“涝坝水”的历史,并让他们住上了做梦都不敢想的水、暖、电和电视等齐全的红砖房。
有人对郭斌的工作方式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团级领导干部,在宏观上管理好就行了,不能事无巨细什么都管。老郭则认为,只要是与老百姓利益有关的事,都不能含糊。
力量源于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郭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
一身清白
比起普通百姓,领导干部会更多地面对诱惑和考验。在领导岗位上真正做到固操守节,承受考验,比常人更难。
“考验”二字,力重千钧。
郭斌经得起考验,因为他对老百姓的利益和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他有着比别人更深层次的理解。
郭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因家庭困难,高中末读完便回乡务农。
22岁那年,郭斌从家乡来到边境186团,报名参加了沙尔梁水库施工队伍。由于他在工作中有较强的组织、指挥、协调能力,不到半年,便被聘任为水库施工队队长。
在186团工程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郭斌带领上百名从全国各地招募来的民工战严寒、斗酷暑。历时八年,肩扛手撬,人挑马拉,全面完成了从水库主体至引水渠、龙口泄水渠等工程的建设。
从此,186团人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历史,他及他率领的民工队伍,为186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86团党委决定,将郭斌分配到团场一连任大田班长,同时将施工队伍人员全部留用分配。郭斌由于表现突出,先后被186团党委任命为副连长、连长、供销科副科长、科长等职,曾连续11次被师、团两级评为先进工作者。
无论是作为掌管年流动资金达三、四千万元的供销科负责人,还是作为主管全团工、交、建和流通行业的主要领导,要想“捞”好处,不须吃、拿、卡、要,就有数不清的人主动送上门来。
郭斌常常告诫下属在廉洁自律上不能干“‘粉条泡进开水里’的事儿,让自己直不起腰来”。他用简单朴实又充满哲理的语言,和自己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连长科长,都是“皇上”。供销科长更是人人垂涎的“肥肉”,每年经过他的手流动的资金高达三、四千万元。有人开玩笑说,郭斌在每笔资金上含糊一个小数点儿,一年也可以弄出好几个万元户来。
当时,郭斌家里十分困难,全家住着50多平方米的危旧房,从老家农村来的父亲双目失明,母亲体弱多病,家属没有工作,两个孩子要上学,投奔他来的亲人一大帮。平时,郭斌狠不得一分钱扳成两半儿用。
但他从没想到要给自己“捞”一分钱。当时正值许多国有流通行业经营者纷纷因经济问题落马的时候,他不但一身清白,还被师党委委以重任。
当上副团长以后,郭斌更加注重严格要求自己。团里上马项目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层层把关,他个人从来不以权干预,经济上的事情更是不插手。
郭斌分管的行业,他必须经常与社会不同层次的人士打交道。作为副团长,他连一件像样的衣物都没有。在团里和连队,他套着几十元一件的夹克衫,脚蹬一双圆口“千层底”布鞋,比普通职工穿得还简朴。出差时在公众场合,不认识的人经常闹出把司机和他身份倒置的笑话。
郭斌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每天的早餐是一个馒头和一碗稀饭,一天生活费顶多10多元钱。到北屯出差,他住宿的招待所房间都是20元以下的,即使到乌鲁木齐出差,他住宿的费用也比规定的标准低得多。
郭斌怕花钱。他每次给家人打电话,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将话说完,常常是家人还没开口说话,手机已经关闭了。
近年来,团场实行办公经费预算管理,郭斌由于业务量太大,每年都要超支上千元,每次到年底结算时他都主动扣除。同事和基层领导得知老郭自动扣除了超支办公经费,也学着他做。
郭斌的弟弟郭炳洪自己买了一辆车在基层一家企业服务期间,因企业不景气亏损倒挂了1万多元的账。这家企业负责人去找团党委替郭炳洪求情适当减免,郭斌得知后,让弟弟一分不少在工资中陆续扣掉了全部倒挂费用。
一次,郭斌为一位哈萨克斯坦客商借了1000元钱解燃眉之急,后来,这位客商非要返还他1000元美金。1000元美金,对于当时每个月只能领到500元生活费的郭斌,相当于妻子喂10头猪的回报。可郭斌说,中国的干部坚决不能干这种事的。当场予以了拒绝。
不平凡的成长经历,使郭斌懂得时时刻刻都要清清白白做人。在老百姓眼里,郭斌就是个在廉政问题上一辈子干干净净的人。
严肃家风
去年9月的一天,郭斌的妻子李正玉在一连一块油葵地地头站了足足20分钟,眼巴巴地看着地里承包户收割剩下的油葵头,最终没下地去捡拾。
家里实在太困难,负担重,老郭鼓励没工作的妻子在家养猪、种菜贴补家用。眼看快入冬了,自留地中的饲草料根本不够几头猪出栏,李正玉第一次想到来捡拾油葵头。走到地头,老郭的嘱咐又让她打消了念头。
老郭经常提醒妻子,团里有规定,职工承包地里的作物没有复收以后,任何人不得私自下地捡拾。作为领导干部家属,一定要带个头。
“做官和做人,都要像‘青石板上摔乌龟’一样,要敢于硬碰硬,才不亏心。”这句话出自郭斌的心。李正玉说,自己最理解老郭用家乡话说这句话的份量有多重。
老郭就是这样做的。即使当了团领导,他还是像一棵永远不会离开大地的大树,枝桠扬得越高,根往泥土里扎得越深,他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职工群众”四个字上。
四年前,团党委新班子成立时,几位刚调到团里的常委不相信副团长还养猪。结果到郭斌家中一看,发现圈里猪壮鸡肥,整个院子还长着绿油油的青菜。
作为直接主管团场工、交、建及流通行业的行政领导,想安排几个人的工作,不用吭声,就会有人考虑的。郭斌从来不把老百姓给予的权利用来谋取个人利益。
郭斌当了“团官”,姐姐、姐夫,弟弟、弟媳都来投奔他,希望能找个工作或者承包土地。郭斌说,186团人多地少,职工都没地种,不能违背原则。他鼓励自己的亲人到货场去当装卸工,甚至捡拾废纸壳、废铜烂铁等垃圾维持生计。
副团长的兄弟姐妹去卖苦力,捡垃圾拉不下脸,郭斌亲自装车卸车给他们看。他说:劳动最光荣!有啥子丢人的?
郭斌的父母原来住的危房被拆迁了,弟弟郭炳洪想说服哥哥,借团里危旧住房的政策,一起给老人买套房子。郭斌一口回绝:那不可能!我们父母不是团里的职工,我又管着这一块儿工作,不能违背政策。再说,我也拿不出钱来。
后来,兄弟俩只好凑了2400多元钱,给老人买了套危旧住房。
郭斌愧对父母,只好平时多到老人身边看看。即使这样,住房相隔30多米,一个月也难见几次面。
为了表示歉意,他每年要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来接济他们。
时至今日,他的父母、姐弟都觉得无法原谅他的“绝情”。
当了6年的“团官”,郭斌两个女儿在生活上比普通职工的孩子过得还可怜。孩子在外地上学期间,老郭和妻子每个星期为他们把馒头烤好带到学校,来节省开支。
他在内心知道自己欠着两个女儿的账,但却只给孩子一颗好心,从来不给孩子一个好脸。
小女儿郭雪梅通过努力,参加师公开考试成了团中学一名教师,去年参加全师语文课卷大赛获得第二名后,满以为爸爸会高兴地表扬一番。可他却说,你离第一名还有一段距离呀!
大女儿郭玉梅参加公开竞聘后,几位常委同他商量说,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入团计财科,他一句话顶了回去:我是副团长,女儿就进团机关不合适。硬是把女儿打发到了基层。
郭斌性格豁达、耿直,为人豪爽。因此,下级和职工群众都喜欢和他来家常,有什么心事也愿意和他沟通交流。
每次和下属出差,凡是生活上的开支,他总是主动付帐,不占一分钱的便宜。向困难职工捐钱、捐物,他都是慷慨解囊,毫不犹豫,率先捐赠,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爱民如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风亮节。
长路相送
“老郭啊,你给我们修好的自来水,你不是还没喝上一口么……”
“郭巴斯,我们工作没做好,你可以批评啊?为啥非要甩手离开我们呢……”
2004年11月15日一大早,186团各基层单位的职工群众自发前来向为
他们奉献了一生的郭副团长送行。
偏远边境连队的职工们挂着晶莹的泪霜赶来了;团部许多的个体工商户们自发歇业一天赶来了;远在190多公里外的农十师领导赶来了;当地县委、政府,驻地海关、口岸委、军警部队赶来了;曾经无法理解你埋怨你的群众赶来了……
沿途大街两旁,行人肃立,为你行注目礼。很多职工和临时工,追着灵车,一直跑到墓地。
前来为你送行的一位吉木乃县委领导说,自己在吉木乃县工作了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撕心裂肺的送葬仪式。
你太忙了。仅10月6日到11月12日一个月零六天的时间里,你除了为团里明年的发展出国考察一次外,还曾三次到乌鲁木齐,三次到师部北屯,10多次深入到全团检查工作,出差行程近1万公里。
2004年11月11日,从团里出发,你就感到了身体不适。可是,你却没舍得到医院去看看。13日上午,快速反应的病情使你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在现场的北屯医院专家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