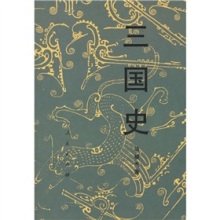凤书三国-第1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越亮;诸葛亮的船队似乎已是很近,而驻守阳泉的船队也横在了淮水中央,准备应战。
三支船队越来越近,五里,三里,两里;待诸葛瑾船队前锋离曹军船只不五六百尺的时候,就只见一支足足六尺余长的弩箭朝着他们的方向飞来,激起风声凌厉仿佛鬼哭。弩箭落在了两艘船之间,但远远望见此景的诸葛瑾已是心下暗惊。曹军的船上竟有这般强劲的弩车!他很清楚,眼前定是一场苦战。
三支船队终于汇集一处,一片火把将周围照得仿佛白昼。江上箭矢纷飞,喊杀声不断,从夜间直战到天明。曹军虽然器械精良,却敌不过对手的船只数目。诸葛亮所统的数十战船上亦有装载弩车。若不是唯恐伤及友军不敢滥用火器,恐怕这一战还能早些结束。即将破晓的时候,诸葛亮终是抓住了机会,围住曹军最大的一艘战船,用火器几番狂轰滥炸,终于击破了曹军的阵势。眼见主力战船渐渐沉没,损失又重,曹军不敢恋战,渐渐退往南岸水寨,意欲倚河岸而守。只是敌军也无心再战;两支船队汇在一处,缓缓逆流而上,往安丰郡退去。
这一路从阳泉到安丰,却还要重编残部,停泊船只,还少不了和荆州军周旋。诸葛瑾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一路撑到安风城中的。直到在弟弟的府中坐下了,他也仍未觉放松。诸葛亮只是几分担忧地看着他,许久方道,“兄长,淮南。。。”
“合肥以北已是尽归曹公,”诸葛瑾应道,“我带来的淮南所有残余兵马船只。如今除了甘兴霸在合肥尚有兵马,其余皆是损失殆尽。”
诸葛亮蹙眉道,“是当涂有变?”
“子敬兄殁了,”诸葛瑾缓缓呼出一口气,尽力平稳地说道,“他旧病复发,终于未能熬过去,去了已有四日。只是我虽嘱军中切莫发丧,终究未能瞒过曹公。子敬方去,他便能领大军扑袭,一举破了肥水上的防线,骑兵连夜直奔当涂。子敬兄不在,当涂还有何人能挡曹公?”
诸葛瑾伸手支住额头,理了理纷乱的思绪,又是续道,“我当领军退往合肥,助兴霸守住合肥;至于这些船只,只能暂时寄放在孔明这里。待将来回了吾主,再来与左将军商议当如何处置。”
诸葛亮迟疑片刻,终是轻声说道,“阿兄,若归去后。。。”
“孔明,”诸葛瑾打断了弟弟的话,温和却不容反驳地说道,“我知道孔明是好意,但此事我本不当与你议论。若擅自议论,终有因私忘公的嫌疑。。”
诸葛亮只得停下,又是默然片刻。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最后却只是微微叹了一口气。
诸葛瑾在安风城中休整了五日,便领着五千余残军出发南下,缓缓退向合肥。淮南的战事僵持直至二十一年的五月,曹操才终于因为雍凉战事退兵。他虽然一直未能夺回合肥,但至少已将合肥以北的淮南全境牢牢握在手中。江东的淮河水军全军覆没,损失了近两万人马,如今却只能背靠合肥这座平原孤城苦苦坚守。这恐怕是自从孙氏盘踞江东以来损失最为惨烈的一战。
诸葛亮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局,尽管他只给兄长去过两封信,甚至还暗自忧虑那两封信是否已经太多。然而江东那边却一直风平浪静,孙权也并没有为这一次溃败做出任何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如此,诸葛亮仍是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孙刘两家联盟只怕是生出了无可弥补的缝隙。
--------------------------------------------------------------------
这篇文我还是要写的真得。。。。。其实之前我一直卡在这淮南大战的最后部分,如今决定把这淮南战役给尽快结束了,然后下面继续书凤的视角。
1。 命数
这一章写得好痛苦,T____T。。。。。我现在还有点不在状态,得慢慢恢复气息了,还请大家海涵,拜~
-----------------------------------------------------------
当我们的车驾终于驶近了成都城中,我已经将战报带来的沮丧忘了大半。看见那熟悉的城墙越来越近,我只有满心的欢欣。其实说起来,成都不过是又一座都城,而我在成都住的时间也不算长,可是如今回到成都,我真得感觉仿佛回家一般。这里有父亲般的主公,有鹃儿和阿斗这两个弟妹,还有阿粲,更别说这么多至交好友。以前我都未曾察觉,但去了许都这一趟后,我才终于意识到,我当真离不开这些人了。
回到府中,不禁阿粲在府中,阿斗居然也与他一起等着我。看见我入内,阿斗冲了出来,抱着我的手臂不肯松开。阿粲却是远远地看着我和荀谌。他微微蹙着眉,脸上的表情很是复杂,带着几分宽慰,但还有几分不安与惶恐。这哪里像是一个十岁孩子该有的神情?我被他看得心头酸楚,却又不知该如何与他说话,也只能问问他的日常起居,问问他的学业,再听他恭恭敬敬地答复,拘束得仿佛陌生人。
我在府中也没呆上多久,将军府便有人来传,说是刘备召我去见。时隔大半年,我终于又见到了他,当真是激动得不能自已。左右周围无人,我也顾不得了,直扑到他怀里,竟是哭得怎么也停不下来。
“好了,好了,”刘备抚着我的背,温声道,“回来便好,本是喜事,怎竟是哭泣?”
“当初在雍州,当真、当真吓坏我了,”我哽咽着说道,“我就怕再也见不着主公了。来这里将近十年,我好不容易找回来一个父亲,难道再要来一次生离死别?”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今年已是建安二十四年,离历史中的白帝城只有四年了。就算这一次不会再有夷陵了,可不是一样有成国渠边的惨败?我不知道刘备是怎样在两万余大军损失殆尽,大将折损的情况下退回来的,但想来也是九死一生的退军。突然之间我更觉恐慌,拉着刘备的袖子,只顾着掉眼泪。
我说了这么一番颠三倒四不吉利的话,刘备也没有在意,只是一味柔声安慰我。他这般模样,我倒是不好意思,止住哭声,擦干了眼泪,勉力收拾了心情认真说道,“我这去一次,当真叫主公破费了,不过我也不算毫无收获。说起来,曹公的邺城乃上古城市规范的佼佼者,我在后世也见过许多次邺城的详图。之前一直不曾想起来这件事,但这次去了邺城,我也留心注意了一下。虽说也未能满城跑过,但是我见到的那一点,足够我结合以前见过的邺城图样画一份详图出来。我尽量赶快弄了,给主公送来;说不定今后什么时候便能用上。”
刘备有些啼笑皆非地看着我,半晌叹道,“到了邺城,你还不知收敛些,竟天天想着这些?还去为曹孟德治什么瘟疫。”
我一愣,不禁嘟囔道,“我本是很收敛的。只是撞上了三哥病倒,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顿了一顿,我终是轻声说道,“对不起,主公,给你添麻烦了;还叫你给曹公送医送药的。”
“这倒罢了,本也是为备造势之事,只是书凤,”刘备拍了拍我的肩膀,缓缓说道,“也是备的不是,成日将你往前线上赶。书凤,今后你还是多留在家中,教导几个孩子,莫要随军出征了。你这番去,当真苦了阿粲这孩子。”
提到阿粲,我又觉心中酸楚。我真是一个很糟糕的母亲。阿粲这才十岁,小小年纪就远离家乡亲友,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可我却将他一个人撩在将军府上,一走就是一年多!如今听得刘备这一席话,我只能沉默。
刘备大约以为我的沉默是不满,便握住我的肩膀,叹道,“备也不是让你就此不出深闺,在家中一心相夫教子。这一来岂不是教备白白损失了一位谋臣?书凤,备或许不曾对你说过心下倚重之情,但在备看来,你与友若、孔明他们亦是一般分量。今后这许多事情仍要书凤为备参商。”好极了;我才哭完,这话差点没把我又惹哭了。我知道自己对刘备有点小用处,但也一直觉得刘备待我更像老父亲对待一个女儿,而没有把我当成正经的谋臣。如今乍听到他这般话语,我只觉得感慨万千,顿时觉得这近十年来所有的艰险都值了。好在我还没真来得及哭出来,刘备却是沉声续道,“如今还有一件大事,备想听听书凤的看法。”
“嗯?”我忙尽量静下心来,“主公,发生什么事了?”
“几日前方才收到的消息,”刘备缓缓说道,“曹孟德自称魏王。”
我一愣,第一反应竟是——令君定然要伤心透了。当初荀彧不顾一切地劝阻曹操称公,直到曹操送上了那空饭盒;但就算荀彧劝不住曹操,淮南的失陷却是终究让曹操无法厚着脸皮在这等失败之后称公称王。但如今他在雍州和淮南接连大胜,果然便按捺不住了。我再侧头看刘备,就只见他面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这些年来我已经学会了看刘备的脸色,可如今我还真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我将那些思绪在脑海里翻覆了半天,终于说道,“主公,其实这并不奇怪;曹操迟早会走这一步的。他年纪大了,总得为子孙后辈着想。或许他现在能独霸朝政,但汉室名器尚在,汉皇尚在;待他去了,他的几个儿子能否也挟制天子?所以他要称王,要封地,这是自然的。”
说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有点理解了。曹操死后曹丕急匆匆地称帝,是否为了在情势尚好的时候彻底断了汉室复辟的可能?如此说起来,我们这儿岂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若无帝王名分在,若是刘备有个三长两短,就凭阿斗这一个孩子的威信,能维持多久?就连孙权都曾有过片刻的统治危机,而阿斗的领导能力又怎能和孙权相比?我差点没脱口而出劝刘备称王,但想想也觉得眼下绝不是他称王的好时机,便终是闭了嘴。
刘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叹道,“不错,书凤此言有理。备本以为,以曹孟德的心性,本不会在乎那点虚名虚位。但他若是去了,这名位对于他的儿女而言便绝非虚幻。他也是年岁大了。”顿了一顿,刘备又是叹道,“这一转眼,离备初识曹公已是廿年有余,吾等都老了,到了该思虑身后事的时候。”
“主公!”我被刘备说得心慌,忙道,“主公正值壮年,为什么说这种话?”
刘备哈哈大笑起来,道,“备明年便六十了,何来壮年?讨备开心不是这般说法!”他又是停下了,这一次静了很久。正当我考虑着改变话题,却突然听见刘备问道,“书凤,以你所知,曹公还有几年,备却又还有几年?”
“主公!!”我突然觉得有些怒了,“主公,我来此已经快十年了,历史也早就变完了。主公为何还要问?我当初便说了,我尽我所能帮助主公,就是因为不愿看见当初那般结局。”
刘备又是微微一笑,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备今有荆、交、益、凉四州,想来是比书凤所知多了许多。只是战场胜负或可变迁,人的寿命能变否?”我又是一愣,还未来得及说什么就听刘备又道,“书凤可是懂些医术?”
我心中的不安越来越盛,忍不住慌乱问道,“主公,你可是病了,可是觉得身体不适?”
“不是备如何,”他摇头道,“孝直病了,病得很重;便是张老都道,拖到如今已是奇迹,怕是拖不过今年了。”说到最后,他那一直平缓的声音终于现出了一丝裂缝。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