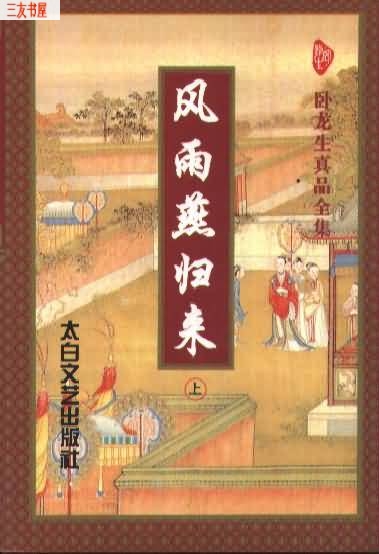�����ž���-��2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Ȼ��ˮ���ϲ�רҵ�������������Ϻ�רҵ�����������ܺ����֮�����ִ��˽����ȥѰ���������ƺ�ˮ����ר���˲š������Ų�����ʲôרҵ�����⣬һ������ר�ŵ��˲ţ�ֻ�ǿ�����������ܲ����ҵõ���
��������ԭ��������һ�����˼�ѱ�ĵͼ�����������μӻƺ������˵��������൱�о��飬�����ķ���������Ϊ�ϲ������ӣ�����һֱ�������š��ž���Ϊ�����Ե������˼�ѱ��̡��˼�ѱ���뵽�����ڸ������ܵ��Լ�������������̣����Ե�ʱ�ͱ�����κ��κ��ġ�
�ž���һ���žͿ����˼�ѱģ��ƺ�ˮ������һЩ�о�ģ�ͣ�һ����֪������һ��ʵ���͵��˲š��������˼�ѱ�й������ƺӵļ�����۵㣬��̸���и���ȷ��������һ���ܸ��µ�ѭ�����������¶����ģ�Խ������˼�ѱ�����ֻƺ������Ĺ�����
ͬʱ��Ϊ�˱�֤���ùٳ��ϵij�Ƥ�ͷ������˼�ѱ��ɲ���Ҫ���鷳���������������ۣ���������ص�ְ�ܲ��źӵ������˺ϲ��ü���һ�������˼�ѱ���������
��ν�����˲��ã����˲��ɡ����ž��������˼�ѱ������������Ȩ����������Ϊ�俪չ����������һ���ϰ���
�˼�ѱ�����Ա��ž�����֪��֮������Ȼ�龫���ǣ��Դ��ǻ۽���˻ƺ�ˮ������������������ܵ����յİ����볯͢�ļν����������ž����������˵������ʵ۶��ž����������㣬�˼�ѱ�������ɣ�վ�������Ϊ�ž����绤�����������˼�ѱ��ʢ������û�ж��żҸϾ�ɱ����
����˵���ž�����֪�����ã�����Ϊ�������������е춨�˼�ʵ���˲Ż�����ҲΪ�Լ���������Ԥ����һ�����벻������Ƹ���
����˵����������˵��Ҳ��˵����Ҳ���ӣ��Ϳ��������ߵ����д����˽�Ļ��ǹ��ġ��ž���һƬ����Ϊ�����ټ�����Ŀ����棬�������������˵������������������������ܹ�˳�����У���Ҳ���������е��¶��ˡ�
������˵�����Ŷ�������Ӵ���һ��������Ŀ����棬Ҳ��������ϸȫ���չ˵������Ż������������ܵĹ������磬Ҳ���ǹ�������Ĺ������磬�Dz��ǻ������˾Ϳ��Ը�������ġ�������������һ�㣬���һ����ĸ�Ч��ת����һ��ջ���
����������˵��ǧ�����������⣬�ž�����λ�����������ֻ���ô���أ�
�뿴�¼���������Ŀ��ɷ�����
��ʮ�彲������ġ����ɷ���
����һ��ϰ�ߣ����Dz�̫�����Լ���
����������Լ������Dz����ţ����Dz������Լ��ļ�������
�����и�ʲô��Ҫ����������һ���Ĺ����ƻ����Ҷ����Ұ�������ȫ�����Լ������ӣ����Ƿ�Ҫ������д�������ɡ�����������һֱ������һ�����ӣ�����д���������Ϻͼ���Ҫ�����£����¼���Ҫ��ѧ����һ��������С���°�ؼҰ����Ž���Ҫ��������ƿ���ͣ��Ҷ�������Ǽ������������ű����ϼǵ�������ճ�����ȥ����ȥ��ɡ�
�����ı������ù��ܶ���ˣ��Ҹ������˸����֣��С����ɲ�����
���˻�Ц�ң�˵�㿴��ȥҲû��ô�ϰ�����ô�������ͱ����ô���ˣ�������������¶����ǵ�д�������ѵ����㶼�Dz�ס��
������˵�������˵�ȱ�㻹�����������¶������Ⲣ������Ҫ��������ɱ�����Ҫԭ��
��֮������ô������ϲ���ÿ��ɲ������¶�������Ϊ��������һλ����ѧϰ��һ�����С���һ���ù�֮���ҷ��֣����������ҵ�����ȷʵ�����˺ܻ�����Ӱ����ı䡣
�����������һ���еĹ�����˭�أ�
��������������ʱ�ڵ��ڸ���������ѧ��ʦ������������Ϊ��������ʷ��Ψһһλ���μҵ��ž�����
���˻�˵�����ǹ�Ū���飬˵ʲô�ž������ڣ��DZ��ӻ���ʲô�����ɲ�������ʵ�������Ǽ��²��£����ַ�����������������ˡ�
��˵��Ҳ�����٣���ʵ��������ɲ�����������Ҳ���Ǹ����²��������ü��²���һ����Ҫ����ʷ�ĽǶ������죬����Դͷ��ȷʵ�������ž�����
���Ҫ˵����Ϊʲô���Ǹ����µı��ӽ��������ɱ��������С����²����ˣ�������Ϊ����ľߴ���Ĺ������������ž�����������ʱ������ԭ���С����ɷ�����
��Ȼ���ž����������������ɷ�����˵�����Ͳ��Ǽ��²���ô���ˡ�
��ô����������ɷ������ײ�������Щ�ط��أ�
����
˵�ɷ�����Ҫ˵���ž���Ҫ������������ʱ����Ҫ���ٵ����������ˡ�
��һ�����⣺�������塣
��Ȼ���������Ǹ������ʣ������ֲ���ҵ����רҵ���������Ρ���Ƥ���á��˸����¡������˰ܵĹ��������������й��Ĺٳ��ϣ��ӹŵ�������Ϊʢ�еġ��Ҽǵá�ë��ϯ��¼������й�һ�����С���ҪմȾ�����������硱��ë��ϯ֮�����̵����Ǿ�˵�������������������ǵ�����������Ҳ�Ѿ��Ǹ������ˡ�
��ʵ�ϣ���������������ʲôʱ��Ҫ��������ɾͣ���һ��Ҫ��Ե������������ǹٳ��Ϲ�������ʢ�е����⡣
����һ������Ĺ���������Ҫ�dz�Ƥ���á��˸����£���ʵ��ֻ�DZ���������Щ����֮���Բ������Ρ��˸����£�����ԭ������Ϊ���Ǹɲ����¡���������ͯҥ�����̹ٳ��ϵĹ�Ա˵��
������ҷ�ף�������Ӽ�����Ĺ�ª����������ࣻ�������������̫���¡�����֮���ӣ���֮�࣬������ھ�������Ļ�����Ӣ������������������ͻ��������ٳ����¡���
����ɰ����ǣ����Խ����ģ����dz��������ѧ�����Ӽ�ģ�������ĵģ��պö���������̨��������ȫ�ģ��������Ź����ָ�������д���ѿ�����������ģ�Ī�����Ļ����ϵĴ�ѧʿ�ǣ�
������Ұʷ�ﻹ���ع�����һ��˾��Ц����˵��һ���������ʱ��ס�꣬�ڶ����糿�ߵ�ʱ��͵�˵�ҵ�һ��ϯ�ӡ��������˷����ˣ���Ť�͵��������ˡ�����ع�Ҫ��͵ϯ�ӵ���λ���̡��Ա�ʦүһ��ɵ���ˣ�˵͵��ϯ�������̣������û�з������ݰɣ�
��֪����λ�ع�һҡͷ��˵��ôû��˾�����ݰ�����ʥ�˲���˵�������ŵ�ϯ�������ԡ���
ʦүһ����Ц�Էǣ��ĵĻ��˼ҿ���˵���ǡ����ŵ���Ϧ�����ԡ�������˼���糿�������������������ԣ��������������У��������Ͼ���ȥ��Ҳû���ź��ˡ������λ������������Ͼ䣬��Ϊ���������ˡ���ϯ���������ϯ����Ҳ�͡������ԡ��ˡ�����һ���عپ���ô��ѧ��������һ�߿�֪ȫ���������ٳ�ʲô��Ҳ�Ϳ����֪�ˡ����¼���Ц�����顤�������顷��
��Ȼ����Ҳ����ֻ��һ��Ц������Ҳ����˵�����⡣����������Щ��ѧ�������ֲ������εĹ���Ϊʲô�ܳ��ٳ��أ�
�Ӹ�����˵�����ǹٳ������������ṩ������һ����Χ���ڹٳ��ϣ����ɶ��������ɣ�ˮƽ��������ƿ���ɼ���������ϵ���ɲ����ϲ����£����������ɣ�������֮ӷ�����͡�����һ���γɣ���ı䣬������ǧ�����ѡ�
���Թ��Ҿ���һ���ˣ���ʹ��ͨ��ͨ��ʹ��������ϵͳ�˸����¡������˰ܣ��Ǿ��ǹ��һ������ܸ�Ч��ת��֢�����ڡ������ž���������һ��������Ѫ����ͨ���硱��ҩ��������Ƕ��������ġ����ɷ�����
�ڶ������⣺�䷨���
����֪��������������������һ���ĸ�䷨�˶�������ʷ�����еĸĸ�䷨�˶�һ�������������ٵ�һ����������������ѭ�ؾɵĹٳ�����ս��ܱ����¹��
��������ʯ�䷨������������һ��������ǹٳ����¶����䷨�˶����Ծ����ơ�
Ϊʲô������أ�
��ʷ���ϵ�Ȼ��˵�����ı䷨��������˾������Щ��Ϊ�����Ĵ�����������档������Ҫ֪����˾����������ʯ�䷨����Ȼ�Ǹ��������ɡ����������ǡ������ɡ�������Ҳ����ʲô���˰�����Ҳ�Ǹ�һ��Ϊ�����ҳ���������������ʯ�䷨�ij�����Ҳ��Ϊ�˹��ҵ�ǰ;���ǣ�ֻ�������dz����ι����Ը�����ʯ��ͬ���ˡ�����ô������Ϊ���Լ�����������������ʯ�䷨���أ�
�ӽ��۵ĽǶ�������һ���ܽ��ǵ�Ȼ�����ģ����͵�ʱ�ľ���������ԣ�ʵ�����Զ��һ�䡰�䷨�����˴�����������桱Ҫ���ӵöࡣ
ʵ���ϣ���ʱһ����ͻ����ì���Ǽ������¾�֮���ϵģ�Ҳ�����·���������ڳɷ�֮���ì����ȡ�����⡣
���й��Ļ�������ڡ��������ֵ��Ļ������ǿɲ�һ�㡣
���ֽ������λ��⣬�����ž���Ļ���Ϣ������������Ҳ�Ƕ�һ���ġ��Ҹ���һֱ��Ϊ����ν��н���ഫ�����𡱾���һ��������������Ļ����������н�����������Ǻ��Ļ���˵���Ǿ��Ǻ��֡�����˵��û�к��֣���û�л���������û�к��֣���Ϊ�Ĵ�Զ��������Ψһ�д�Ļ��������Ͳ�������������
�����С����顱֮˵������ָ�������ֵ����ַ��������������Ρ�ָ�¡����⣬��������������Ϊ�DZȽ���Ҫ�ġ����dz�˵һ���ʽС��������塱�����������ǰ�������������õģ����ӿ۵ĽǶȿ��������������аٷ�֮��ʮ���ϵ����ǿ���ͨ�������ġ����������塱���ġ�
����˵�����ڡ��������֡����桱�ӡ�ʾ�����ԣ������ʾ������ָ�����Ǽ������˼�����ҡ�����λ�����Σ����ԡ��桱���Ǽ��벿��������ȡ����ڡ�Ҳ������������ͷ�����Ǹ���ʾ�������ǡ��桱�ֵ�ƫ�ԣ���ȻҲ�Ǽ������˼�����������ͷ������֪����ָ���ӣ���������ʱ�ڣ�Ҳ���Ǽ���ʱ�ڣ����������Ҫ���ܲ���ֻ�Ǹ��˾�ס�ģ�����Ҫ�Ĺ�����ָ�������Ȼ�����ĵط������Ե�ʱ��һ����Ҫ�ļ�����ʽ�ͽС��Ҽ�����½�β����о�ʫ�������ʦ������ԭ�գ��Ҽ����������̡������ԡ��ҡ�����ֵ��������һͷ����������ָ����Ұ�����ǵ�ʱ����Ҫ��Ʒ֮һ���ܶ��˶������ס��ҡ���Ϊʲô��������Ů�ˣ�����һͷ���������������
�������������ڡ������ִ����ľ���Զ�������ļ����Ļ���
Ҫ֪�����ӷ���ѧ�ĽǶ���������һ�ֹ۵����Ϊ��������һ�������������Ҳ���ۺ���������ʽ�����ǴӼ����Ļ���չ���ġ������������������������Զԡ����ڡ�����Ҫ���ڶ���Ĥ�ݵ����ߵ�λ�����������������Ǿ��������������桱�����й��Ŵ���Ȩ����һ���ֵ䡶˵�Ľ��֡���Ҳ˵�����ڣ�������Ҳ����һ�������־Ϳ��Կ��������ڡ����й���ͳ�Ļ����������ϵĵ�λ�ˡ�
���dz�����ôһ�������ѧ���Ļ�ѧ����ƪ����Ϊ��Ҫ˵�������Լ����ڶ������Ĺ���ڹŴ������Ժ��������������ϵĵ�λ�����䷨����Ҫ���£�Ҫ���¾ͺ�������Ҫ�����ڶ��µĹ�ء�Ҳ���ǡ����ڳɷ�����ִ��������й����ִ�ͳ�Ļ���������Ե����������ˡ�����Ҳ���й��⽨���ʱ�ڣ������ij��Ĵ����䷨�������ѵ�һ���ؼ���
����ʯ���������⣬����ô����أ�
������һ�侪�춯�صĿںš���˵������䲻��壬���Բ�����������֮�������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