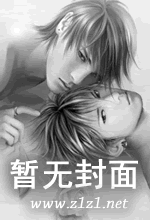企业目的:伟大公司的起点-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需要对自己抉择和行动的原因有一个一致而清晰的认识。那些能和公司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并能因时制宜调整战略的人,将被回报以高职衔、大职权和高薪水。万众喝彩,掌声雷鸣,丰厚的回馈只属于真正的英雄,那些心怀目的的领导者们,与急功近利无缘。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2)
我相信人们最想从工作中获得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目的。当然,别搞错了:人们确实需要酬劳,也有人会需要头衔用于自我肯定。但更多的是,人们想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也想让生活有其存在的理由。中世纪建造大教堂的工匠们不存在任何私心地勤力工作,即使这些教堂一直建到他们孙辈的时代都无法完工,工匠们也不在乎这个。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更努力的。有什么能比为上帝工作更重要的呢?巴赫在他的作品结尾标上字符SDG—“荣誉唯归于上帝”。在这个大作曲家看来,他自己只是上帝的一个信使而已。然而,不一定非得是宗教徒或艺术家才能拥有人生的目的。想拥有目的,你只需看透当世物质文化的虚无,一旦领悟到这一点,目的对你来说就意义非凡了。
※
对我来说,关于目的的观点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在我将从雅典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被指定发表告别演说,所以那天本应该是非常喜庆的一天。然而,我却在痛心和愤懑中啜泣:痛心的是,我的祖国遭到土耳其军队的再次入侵,许多希腊人民死于铁蹄之下;愤懑的是,在上校政权统治期间,两名警察曾将我“请”去警察局“接受问询”;而他们竟也作为毕业班的成员去听我的告别致辞。当时与他们共处一室的我,考虑着要不要在我的演讲中提到那件传讯审问的事。我应该就这么算了吗?最终,对祖国的痛心占了上风,我忍住了自己的愤怒。
到那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变得更加彷徨了。塞浦路斯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以至于我很难专心研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到了第二年,我陷入了窘境,我告诉我的一个教授:“这些理论都很好,但我想学习的是能应用到现实当中、能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论—因为我要为我的祖国贡献一点力量。”他让我去见哈佛法学院的罗杰·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当时正在研究新式的谈判攻略,而那正是我想学习的。我同费希尔教授的研究小组一道研发并开创了哈佛的第一门谈判课程。我还参加了美国国会竞选,希望能颁布土耳其武器禁运的法案。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美国法律是不允许外国人参政的,所以我冒了被驱逐的风险,但我一定得为拯救我的祖国做点贡献。
费希尔教授的谈判课程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第三大最受欢迎的课程,并被美国许多专业学校应用。在帮助费希尔教授写书构思—即后来的畅销书《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我还亲自教授了几年这门课程。1978年,我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单边谈判文本”的研发,在“戴维营和平协议”的签署中,前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运用了这项谈判策略并达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协议。三年后,我被任命为哈佛大学谈判项目中的高级顾问。
但是,学术之外的世界仍然吸引着我。1982年,我被任命为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的欧洲与中东商业发展部门负责人。期间,我提出了“补偿”(offset)一词,并整合了第一个“补偿计划”,以支持西屋电气公司的国防装备分公司—F…16战机的主要供应商。是的,我希望推动和平进程,希望看见和平条约的签署,但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正是冷战时期,我们根本无法谈判。我有意进入了美国国防业,只想着最好能从激进分子的手中挽救回希腊,也可以说,我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继续战斗。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策划了将F…16战机用于对希腊的“商业销售”被指控。我承认自己这么做了,从开始向希腊出售F…16战机起,我就没听说过还有商业销售军用飞机这回事。当时美国和希腊政府之间互不通话,双方关系处于相当严峻的紧张态势,想要这第一批40架F…16战机能运往希腊,我必须采用“商业销售”这一方式。我的目的不仅是想牵制苏联,更是为防止希腊的军事弱势和政治孤立状态被土耳其所利用,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如果说当时有什么信念支撑着我那样运筹帷幄、坚定不移、夜以继日地连年工作,那肯定不是因为我作为国防设备订约部雇员所拿的薪水,而是因为我心怀目的。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3)
虽然F…16战机的购入受到了希腊中立派们的强烈支持,但是仍有那么一个群体持反对意见,甚至比希腊激进分子的反对更甚。希腊极右派人士谴责我对此项销售的推动,因为这延长了以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为首的执政党的掌权时间,但是,我的目的要求我对这一切权利政治和金钱因素都不予考虑。
后来我从西屋电气公司跳到了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并在1984年,被提升为该公司最年轻的项目主管。五年之后,我辞职了。我飞往希腊去看望我父亲,他已是风烛残年,体力渐渐不支。
※
无论如何,我对父亲已经尽到了责任。事实上,作为奖励,我可以拥有一段个人的“休闲时光”。我要求通用动力公司送我去哈佛商学院进修两年,这样我就能继续研究那个我一直困惑的问题:目的和成就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消除恶势力,二来可以为人们造福,我甚至能隐约预见到一个新职业—将想法付诸行动的职业。它不只是要完成一般的结果,还要真实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我采用的方式,就是使公司更具效率,更能充分地实现目的。
我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时将近40岁。1992年从那里毕业之后,我进入由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和傅马克创办的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公司工作。在帮助客户公司分析它们所出现的问题时,我发现了一件别人都没有在意的事—这些公司的问题大多在于它们缺乏理想。让公司变得更具效率是一个太抽象的目的,所以如果要想成为更优秀的公司,必须以先培养出更优秀的领导者为途径。从1994年到1996年在主管摩立特集团的全球性人员招聘期间,我有机会来验证了这条途径。我面试并录用过上百个新人,他们中有工商管理硕士,也有大学毕业生,所以我对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抱负已经了然于心。
招聘的底线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振奋公司的内部士气。一些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们会联络我们公司的内部人员—也是他们曾经的学长。与应聘者个人素质展示和其所拥有的社会经验相比,我们更看重公司内部员工的推荐,因而他们的推荐在招聘新人时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点尤其适用于外国留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紧密联系的小圈子,同时,由于认识到外国留学生对于像摩立特这样一个中型企业在全球的发展中有多么至关重要,因而他们是我特别乐意吸收的人才。
之后,作为摩立特公司的亚欧地区总裁,我和客户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的带领下公司在土耳其、阿联酋、俄罗斯、希腊、德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国家壮大起来。瓦利德·伊斯坎达尔(Waleed Iskandar)—谨以此书献给他和其他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们。他们都期望自己的个性化职业发展需求能受到重视,并强调愉悦、互助的团体氛围所发挥的功能。正是他们首次激发了我的一些想法,后来成为我在潘希亚公司工作时的座右铭:“公司成长的最佳途径是使员工得到成长。”摩立特公司在亚欧地区的确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我至今仍为我们团队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后来,我担任了摩立特公司在欧洲、亚欧内陆、非洲和中东地区分部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并要应对当时网络革命对咨询业造成的空前冲击。时代改变了,要同那些网络公司竞争,我们就无法维持既有的薪酬水平,我们处于被动的防御状态。然而历史教会了我:侵略战争中激励士气的最好办法是利用意识形态,而防御战争中稳定军心的最佳方式则是培养爱国精神。所以在瓦利德的帮助下,我呼吁公司的年轻员工忠实公司,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结果,我们在欧洲没有流失一个员工,而且,由于新出台的股权方案和重整的顾问培训项目又吸引了其他公司新老员工的关注,我们的队伍反而得以壮大。
2004年,从摩立特公司辞职后,我潜心于阅读和思考并随后撰写了此书。而这一段期间产生的想法也促使我后来决定加入潘希亚公司—这家公司为企业提供战略领导方面的咨询服务。理论上讲,我们希望把导致企业成功的多种因素与领导对企业的影响力综合起来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携手合作,共同对涉及到改变战略、领导方向和企业实力等重大问题出谋划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4)
一路走来,我需要和各种不同的观点对峙,有来自我本身的质疑,也有他人提出的挑战,这些观点都让人难以看清楚企业目的的价值,其中一个错误观点就是盲目推崇“个性”,认为它是成功的基础。商业巨头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曾说:“在危急时刻,个性决定处理问题的风格。”可是,对于那些坚信仅依靠其个性便能化解危机的自负者们,只要危机中遇到的困难伤及他们的自尊,这种风格恐怕就会转变为惶恐和不知所措了。相比之下,了解企业目的的人,更愿意遵循古老的求学途径—失败了再来,再失败再来,直至最终成功。
我不得不一再与之较量的另一种观点是神奇式思考。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指望着某个强于他们的人物—类似于拥有神奇力量的家长—能现身危难之中,救他们于水火,这就造成了首席执行官被员工们当成摩西甚至上帝一样来崇拜的现象。他无所不知,能力超凡,只要他的领导不经历失败,员工们就会一直认为自己的领导无所不能。但是,一旦这位卓绝非凡的执行官遭遇失败,人们便认定是这个领导出了差错,甚至认为他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人们不明白的是,如果缺乏明确的目的,任何身处领导之位的人都会遭到失败。
我遇见此类缺乏目的的例子越多,就越发认识到,企业目的于人于我都有极高价值。当今世界我们也许并不知道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问题,但是却需要从企业目的当中寻求问题的答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竞争让我们受益匪浅,但“我们在为何而竞争?”这个问题却始终困惑着我们。如今,全球的企业领导者们对这个问题日益关注,一些领导者把探寻为何而竞争视为使命,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视“做正确的事”为第一要务。特别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与我所敬仰的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们的对话,从日报头版上有关重大问题的报道中—我能看出,当今企业的思维前沿已经由苦求“我们该怎样达到目的?”回归为“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和“为什么应该达到那样的�
![[夏目同人]夏目的幸福人~妻生活~封面](http://www.xxdzs3.com/cover/7/7373.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