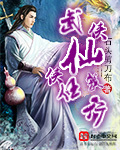������˵-��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ȫ�ĺ�����Ϊ����ļ��DZ�����������һ����ʽ������ȫ�濼�ǽ�������л����˿����е������ͥס��������ļ����ļ��ij�̨���˵����������ʼ������е������ͥ��ס�����������������ճ̣�����ʼ������������������Ρ�
���������ļ��м��ж���״�ķ��������жԱ��϶���������õص�����ķ�����ͬʱ�Ծ�������ס�������ⷿ���������ԵĽ�����������͡������������Ĵ��λ�á���ͨ״�����������������������������Ȼ�ļ���û�и���ס���ķ��䷽ʽ���Ȿ���ǡ��滮��Ӧ��������⣩�������������֪������������ʵ��Щ��Դ��ר������е������ͥ��ס����������
�������Һܲ�������ǣ��������е����ü��߶�û�п�����һ��Ϣ��û���˹�ע���滮���Ա������е������ͥ�ĸ�����û���˿��������������ڿ�ʼ��ע�ؾ��ý���ת����ע���е������ͥ����ᱣ���ϡ����м��ߵ����ʶ�����ָ������Ҫ��������Ʒ�����������佨15������ᱣ����ס������Ϊ�������ڽ������Ƹ��г��Ϳ����̣���Ϊ����Ʒ�������н��豣����ס����Ӱ�������ߵĹ�����ѡ���Լ�Ӱ����Ʒ��������Ʒ�ʵȡ�
����Ϊʲôý��Ͳ��ܴ�����������������������е������ͥס����������������أ�Ϊʲôý��Ͳ������е������ͥ���һ�����õ�Ԥ���أ�
�������滮���������Ǹ���ʮһ�塱�ڼ�Ķ�����Ϊ�������佨���ص���ȷ���ض���һЩ���������滮���������˳�ֵ���أ�����ͨҪ���ܱߣ��������������Ĺ�ע�㣬�Լ�Ϊ��ֹ���������ò������ɢ��С���С��ؽ��н��衣
��������ȫ�������������Ը�������ⷿ�Ŀ��ԣ���1�������½�������������ڵIJ�������֧������2���������ӳ��ڹ������ѣ���3�������˽�ͨ����ҵ�����ѣ���4��һ����ͥ�����뷢���仯���������˳����ͻ���ֳ���ռ���ʽ�����⡣
������ˣ��������ⷿԶ���緢��ס�������ã����û����оͽ����ͱ��ⷿ������һ����ͥ������ߣ������Ϳ�����ֹ����������ԴתΪ�������˵IJ�����
����ý��ܹ����Ҷ�����Ʒ��С�����佨������������ƺ����Ϊ������õص���Լ�����������Dz�֪�����������ʵ�ס��������ͬһ��С����ͬһ��¥�е���������DZ����������Ĵ��٣��������������������������ѷ��������¡�
�������ڼ���ǰ��������ص�һЩ�ز���ҵ��Ա��ͬ���������ױ��Ǵ�ѧ����ʱ����ר�Ųι��˹��������������Ŀ�Ĺ��̣�����ר���˸������Ŀ���칤�̵Ŀ����̣�Ҳ�ι�����Ŀ������䣬�˽�ȫ���������ڹ�����������һ��С���зֱ����������ַ��������Ҳ����ͬһ�������У���2/3�����������������������ͥ���۷���1/3��������費�۵���Ʒ���������
�����ڹ��������۷��ļ۸�ԼΪ2��000~2��800��Ԫ/ƽ���ף���Ʒ���ļ۸�ԼΪ3��500~4��800��Ԫ/ƽ���ס��۷������۶�����ҪΪ��������75��000��Ԫ���µļ�ͥ��һ��ΪС��ʦ��ҽ����Ա�ȣ�����Ʒ������Ҫ���۶���Ϊ��������100��000~140��000��Ԫ֮��ļ�ͥ��
����ŦԼ��������ס���۸�ܹ���Ϊ4~6����Ԫ/ƽ���ף��е������ﵽ10����Ԫ/ƽ���ס�����������ŦԼ�ϵ�������Ⱥ�ľ�ס�����������Ժ���Ϊ����ƶ��������ŦԼ�е��ؽ������У������ڹ�����Ͷ���˴����ʽ���Ż����ߣ�ϣ����һ�����ܳ�ΪŦԼ�µ�һ����죨�е����룩�ľ�ס�����Ը�����һ�����ġ�ƶ����������ȥ�ι�ʱ�ѳ�����Ч�ˡ�
�����뱱�����й滮�ļ���ͬ���ǣ�����������һ��������ס�������ƶȡ��۷��������������ʲ��������е����������ͥ���ס�������һ�ַ�ʽ�����������������ת��֧���ı�����ס��������������ҵ�����뿪����֮���һ�ֽ����������ؼ۸��еIJ����������ʽ�����еĵ�Ϣ������˰���еIJ����ȣ����۷�������Ŀ���ʱ��ر�������40�����ϡ�
�����ڱ����еĹ滮�У�������������������Ϊ������ס����û���κε����������������в�δͶ���κ��ʽ��벹��֧�֣��õ����Ǿ��ؼۡ������۵ķ�ʽ��
���������ԣ�����û���κ���λ���ı������Ȳ���ȫ���˴��������Ҳ���ǹ���Ժ���ļ���Ȩ������������Ժ��ίһ�������������ļ���û�С����ǡ��滮�������˸���������������������ñ�ӣ������Ե�������������ͷ�ϡ�
���������Ҷ�����û����λ�������п���������3��000��ƽ����ס�����ɻ��ƽ�ֱ�����ƽ�����ۺͽ�����ֵ������ͥ��ס�����Ѵ����ô�������Ҳδ�ز���������̴����ô���
������һ����Ʒ��С���������������ָ�꣬Ҳ�����С���Ľ���ɱ���ʡȥ����ԭ�����ܳ��ֵ�������ֵ˰�����ò��۵���Ʒ�����ּ۸���ߡ�
����������Σ������ó���һ������������ס����������Ʒס����ʵʩ�滮��˵��������Ŭ����Ϊ����е������ͥ��ס��������취���������л���������������ͻ�����⣬����ִ���е�ϸ�����⣬���ܱ�û�мƻ�Ҫ���ؽ���һ����
������2007��7��20�գ�
����
��������
һƿ����ˮ���������������Լ��1��Ǯ���������ۺ������������10������Լ1��Ǯ������ƿˮ������С�ݣ�����������10������Լ�����1ԪǮ������ƿˮ�����˴꣬������10������Լ�ͱ����10ԪǮ��ͬ����һƿˮ�������г�֮��ˮ����������װ��û�����仯�����۸�ȴ�����˾�仯��������Լ1��000������ֱ�Dz���˼�飡
������ͳ�ľ���ѧ��Ϊ�����������ܴ���Ƹ�����Ϊ�����Ĺ����б������ﲢδ�����仯��һֻ���ӻ�һֻ��������֮�����ӻ������ӣ������Ǽ�����δ������������ֵ����ʵ���ϣ������ӵ���Ҳ���������������������ijɱ���������ӻ��ߣ���֮����������Ҳ������ͬ�������⡣���ǣ��г��в����˽���������ͨ�������ø��Ե�����õ����㡣
��������ͬ�����н��ijɱ�������ɱ����ڽ����в�����ֵ�Ĵ��죬�����Ӧ�е�������Ƹ���
����֮����һƿˮ����������������ͣ���Ϊ���������⼼�������IJ�Ʒ���ԣ������ߵ��Զ�������������γ���������ҵ�Խ��ͳɱ������Ҳ��е����۵Ľ��׳ɱ��������õ�������Ϊ����������ȡ�������۵ijɹ���
����ˮ�����ۻ�������������ȳɱ������Լ۸����˱仯��������Ҳ�õ��˷��㡢���ܵ��˷��������̻�ȡ�˸��������ߵ�����
������ˮ�����˲ݣ������������ۻ���֮�����ܵ��˲��������ߵȷ������֧�����ݸ��ߵļ۸ݻ�ȡ�˸������۵�����
������ˮ�����˴꣬�����������ܵ��˸��õķ������������¶ȡ��ɾ��������ȣ������ȡ�˸��ڲݵ�����
����һƿͬ����ˮ�������������۵ĸ������ڣ�֧���ļ۸������������ˡ�ˮ��Ȼ��ԭ����ˮ������������Ը֧�����벻ͬ�������Ӧ�ļ۸�
����һƿˮ�����۵����ϴ�IJ������������ߴӻ������������ݳ����ѵĹ��̣�ͬʱҲ�����������仯�Ĺ��̣������Ľ���Ҳ��������������������Ĺ����С�
����ס��������������ͬ��������һ���仯�Ĺ��̡��������ͥ�������ٵ��ǽ����������⣬���ⷿ��ԼҪ�е���Ҫ�ı���ְ�ܣ��൱��ˮ�����۽Σ��е������ͥ���������ס�������൱��ˮ������С�ݣ����������ͥΪ�����������������ߵ�ס�������൱��ˮ���˴꣬��һ�ֳ���������֮��ľ������ܡ�
���������������������ߴ������ֵ�ѡ���иߵ����ݳ�Ʒ��Ҳ�д������ͳ���������֮��ļ۸�Ҳ�����ٱ�ǧ������ȴ��δ����ȥ������ɱ�֮��IJ����Ϊ���а�����������������������������óɱ�������ġ�������Ҳ��δ�Լ۸������κβ�ͬ������������ý�����Ϊȷ�����ַ�������Ʒ�IJ��
����һƿˮ�ڸı乩�����������ѱ���ʱ���Բ��Ƴɱ���������ᶼ�ܽ�����۸�������ı仯�����ǵ�ס�����ṩ���ֲ������ʱ��ijЩ��ȴ�����ͳһ�ɱ����㡣
����ס��Զ��һƿˮ���Ÿ����ӵ��������̼����ߵļ���������ȴ����Ϊֻ�ܼ���ԭ�ϵijɱ��ͼ۸������DZ���Ϊ���ܷ�������ı仯��
���������ǿ��������ģ���ס������������ȴ����ʹ������۸���֮�ı䡣ֻ�����������ܸߵ�����ȴ�����ṩ��������۸����������������������
����������ᶼ�ڹ�����̼���Ʒ��������������ֻ��ס���������������ƣ�����������Ϊ����б��Ҳ�������й����÷�չ������Σ�����Ʒ��ȴ����е����������������Ρ�
�������غ�ˮһ��������һ��ϡȱ����Դ�����˾����㣬�й��ƺ�û��ʲô��Դ����ϡȱ�ġ�����������ʱ����Щϡȱ��Դ�����ü۸���е����������й���Զ�������Դ��ϡȱ���⡣
������Դ��ϡȱ�����ܳ�Ϊ�����������������ɣ���֮��ǡǡ�����������еIJƸ����켰�۸�������������ϡȱ����Դ�ع鵽�����������У����������������߽��ܺ�������Դ�۸�
����ס�����ѵ�������Ȼ��Ϊ����г���������ͬʱҲ�Ǵ����������ѵĻ��������۴��ĸ��Ƕȿ�����ס���������������ƶ��Dz���ʱ�˵ģ������������еļ۸��������г������һ����֪��һƿˮ�������1��Ǯ���10ԪǮ���������Ҳ����˵�ǡ���ĭ����
������2008��1��7�գ�
�����������顡������վ
ƶ����������
�ڽ��ܲIJɷ��б��ʵ��������Ҷ�ƶ������ޣ��ƺ��ҿ��������ˡ�����ֻ����Сƽͬ־�Ļ����ش𡪡���ƶ���������塱��
��������һ��������Ա���������걻��Ϊ�С������ġ����㹲����Ա�����������֪���������Ǵ������˵�����ġ�1949��ĸ����ɹ��������˳�Ϊ���������ˣ��������������˲����ǹ������ķܶ�Ŀ�꣬ʵ�ֹ��������ǰ�������ʵļ���ḻ�������е����˲���ƶ����ǹ������ķܶ�Ŀ�ꡣ
�����ĸ↑��ǰ�ļ�ʮ�꣬�й������˲�δʵ�ָ�ԣ��Ŀ�ꡣ
������Сƽͬ־�������ʶ�������ʵ�ʣ�������ʷ��ǰ���ĸĸ��˶����й���ʼ�˴�ƶ������ԣ�ĵ�·��
���������ǵĸĸ���ȴʼ�����������������˶���ɸ��˵�Ŀ������ij���̬�����һ�ᵽ���������ˡ��ͳ��˴��������ģ������ˡ��������˱���������ڸ߶��ϿɵĹ�ʶ����ô�й�������������е����˶���ɸ��˲�ʵ�ֹ��������أ����ƶ��ܱ�������������Զ��һ�����������ʵ�֡����������ԡ�����˵�����������������������أ�
�����������쵼�Ĺ��ҵ�ȻҪ�����д���ƶ������˵����档���ȣ�Ҫ�����ҵ�ת��֧������Σ�Ҫ�����İ����������������������ϡ�������Ҫ���ǣ�Ҫ�������Թ�ƽ�������¸������������������Dz��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