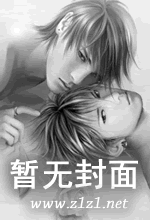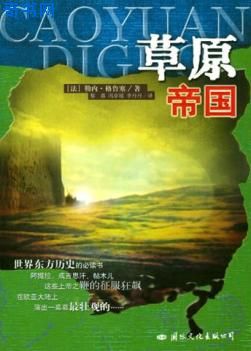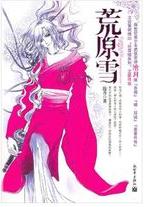大平原-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船一拨人一拨人地渡着,这八口大舍锅,一马勺一马勺地为大家盛粥。我们家这口锅前,奶奶烧火,爷爷掌大马瓢,高大一担一担地从渭河里担水,往这铁锅里续水,高二和高三,这两个半大小子也没闲着,他俩从家门口背来苞谷秆和麦秸草,充当柴火。桃儿刚会走路,于是像一只猫一样地蜷在高安氏的怀里,屁股蛋子坐在高安氏盘起的腿上。
我的苦命的母亲那一年六岁。她也在这一支从黄泛区来的庞大的逃难队伍中,来和我的父亲高二赴这千年之约。此刻她正在路上走着,她将在三天三夜之后,即这一支饥饿大军的行走接近尾声时到达。她姗姗来迟的原因是在逃难的路上,有一个姐姐卖给路经的一户人家了。这事耽搁了这户人家一点行路的时间。
渭河岸边高家渡这一场舍饭,发放了三天三夜。渭河的水担了多少担,无法去量,能够丈量的是我家门口顺墙而立的那一大簇苞谷秆,全都烧光了,一个麦秸垛,也烧光了。下锅用的那玉米子,是一条船上运来的。那时渭河上还可以行船。一条涂着红色和蓝色线条的船,在渭河这一段河岸来来回回地走着,不时地卸下粮口袋来。那船上,一个穿一身白西服的城里女人,甲板上放一个凳子,她坐着,抽着烟卷,面无表情地看着岸边。
高家渡的渡船,使的是篙。一根丈二杆上,前面是一个铁尖,后面是一个把手。船工以篙点地,叫一声“船开不等岸边人”,身子往起一跃,将篙的这头往怀里一压,篙身压住船身,船一倾斜,这船就离岸了。
人太多,船渡不过来,因此这三天三夜里,老崖底下的人群挤成了疙瘩。等船的人中,有蹲在地上抽闷烟的,有全家人倚着老崖晒太阳的,还有些妇女,到河边去洗脸和梳头的。而到了夜来,火光燃起,高家渡上更是热闹。
“穷欢乐,富忧愁,讨吃的不唱怕干球!”说这话的是一个耍猴的河南人。在中国地面流浪的河南人,耍猴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谋生手段。这个离乡背井的耍猴人,真可怜了个他,什么家当都没有了,只肩膀上卧着一只猴子。
夜来火光下,那河南来的耍猴人,把锣儿“当当当”地一敲,将猴子从肩膀上一甩,甩到空里,又用手接住,他开始耍猴了。耍过一通后,场子圆了,接着一个扎着大辫子,浓眉大眼厚嘴唇的姑娘,开始唱河南梆子。她唱得真好,博得四周一片喝彩声。这一群河南人因了这歌声,在一瞬间有了一丝温暖,差点忘了这是在异乡,在陕西境内渭河岸边一个叫高家渡的荒凉堤岸上。
我的爷爷后来曾无数次地说过,那个在西安城里唱红、在郑州城里达到功德圆满的豫剧名角常香玉,就是在高家渡那个夜晚唱河南梆子的大辫子姑娘。他赌咒发誓说“就是她”!
第八章 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1)
正当高家的一家老小,在渭河畔的二崖上,守着一口大锅,从事那场积德行善的善举时,高家的另一个传奇人物,六岁的顾兰子,正拄着一根枣木拐杖,在这支饥饿大军的尾部行走着。她现在还不是高家的人,她将在随后的黄龙山岁月中加入,而就在这次,她还将在这高家渡的官道上,上演一幕戏剧。
那一年顾兰子六岁。母亲把她的开裆裤用线缝住,缝成死裆,然后,把她蓬松的头发用梳子梳整齐,再用两个指甲盖,把头发里那些虱子下的卵(那叫虮子)咯嘣嘣地挤死,然后将头发梳成两个小辫,小辫的根部用红头绳扎紧。“你六岁了!”母亲说。
六岁的顾兰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她只去过一次许昌城。因此,她在描述那花园口决口时所用的比喻,总是说那水头黑压压的,像许昌城的城墙一样高,一样宽。水头翻滚着,就将她的那个小小的顾村吞没了。
她的那个村子叫顾村,这个村子又分前顾村和后顾村。顾兰子是住前顾村或后顾村的,她已经记不起了。她只记得这个豫东地面的县名叫扶沟县,而顾村距扶沟县城三十里地。
洪水涌进顾村的那一刻,全家人顺着梯子,爬到了屋顶。水头顺着村子西头那条小河渠走了一部分,这就是顾村没有顷刻陷入灭顶之灾的原因。但是这土坯房,不经泡。水头过去以后,水还在一波一波地涌过来,三天头上,房子倒了,于是全家人又一个拉一个,攀上了院子里那棵皂角树。已经七天了,这水还没有减弱的意思。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好在这时候漂来了一块门板,于是全家人跳进水里,抓起这块门板,任水漂着他们走。黄河里的水是黄泥汤,人在水里,想沉也沉不下去,所以他们没有淹死。而那门板的作用,只是像把这一家人聚拢在一起的一个物什。
不知道漂了多少时间,也不知漂了多少里路程,最后这水成了死水了,于是他们弃了门板,踩着齐腰深的水,走到干地上。
顾兰子是在郑州城第一次吃的舍饭。那是白米饭,白花花的大米尽饱吃。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吃大米饭,或许还是她生平第一次吃饱饭,所以,她记得很深。
这个河南黄泛区人家也是受了那“天堂般美好的黄龙山”的宣传蛊惑,才踏上这条道路的。最初,从黄泛区出来以后,他们在陕西和河南交界的地方住过一些时日,男人给当地一家打短工,女人给另一家奶孩子。这时候国民党来抓丁,三丁抽一,东家不想让自己的三个孩子从军,于是商量着,商量着天黑以后把这个短工捆起来,拉到乡公所去顶。这话让男人听到了,于是逃了出来。这样,这户河南人只好再走,最后走到了这支逃难大军中。
前面谈过,在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们还将最大的那个孩子卖给了当地一户人家。这个女孩的身价是二斗黑豆。这二斗黑豆现在在担子的一头,而担子的另一头,一个笸箩里装着三个孩子,那是顾兰子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这二斗黑豆将是这户人家在去那黄龙山的迢遥道路上的全部吃食。
顾兰子已经六岁了,她能走,因此她是独自一个人走着的。路旁的所有的野菜和能吃的树皮都被采光了。但是行走间,眼尖的顾兰子竟然在不知哪个角落摘到了一枝蒲公英。母亲难得地笑了笑,她把蒲公英叶子放在口里嚼了嚼,将那汁子吐给笸箩里熟睡着的孩子们。然后将那一朵黄色的蒲公英花,给顾兰子戴上。
第八章 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2)
“等到了黄龙山,安顿下来以后,我用老婆针烧红,给你耳朵上穿两个耳朵眼。一人一个命,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说不定,你这耳朵上,将来要戴金挂银呢!”母亲充满憧憬地说。
“我不穿,我怕疼!”顾兰子说。
顾兰子行走着。早春的平原上的阳光,照着那黄花,一炫一炫的。但是很快,顾兰子就想吃它了,瞅母亲不注意,她把那花从头上摘下来,满把手握住,塞进了嘴。
前面又要经过一个村子了。这个村子和顾兰子所经过的那些陕西村子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被一簇树罩着,四合院子,揭背厦子,那揭背厦子的褐色的厦背,从树荫中隐约露出。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牛车道,从村子的中间穿过。“高家渡,高家渡!要在这里渡渭河!”女孩听人群嚷嚷道。
这时候只见一个半大的孩子,脑后巴子剃得精光,前面留一个盖盖,手里拿一样什么东西,正两步一颠,三步一顿,跳跳蹦蹦地从老崖上上来,走上了高村的官道。
那半大小子边走边哼唧着一首平原地面流行的口歌:
墙上一枝蒿,
长得渐渐高。
骑白马,
挎腰刀。
腰刀长,
杀个羊。
羊有血,
杀个鳖。
鳖有蛋,
杀个雁。
雁高走,
杀个狗。
狗有油,
炸个麻糖滋漉漉。
东头来了个麦秸猴,
头发梳得光溜溜。
…………
顾兰子并没有注意那孩子的歌声,她的目光,她的全部的注意力现在被孩子手中的那个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个热腾腾的蒸馍,一边冒着热气,一边还在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麦香。大约,这只蒸馍是在大舍锅底下的麦秸灰里刚刚煨过,表皮还有一层薄薄的焦黄。
女孩以为自己是饿昏了,是眼睛看花了,她停住脚定睛细看,见那向她迎面走来的半大小子,手里确实是拿着一个蒸馍。
在这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即便是平原上最殷实的人家,也没有这样的好吃食呀!
那迎面过来的半大小子叫高二,也就是后来的我的父亲。那一年他十岁。
那一天早上,高二的小脚特别地勤,抱苞谷秆抱了一趟又一趟。祖母说:“我娃跑得真欢!”祖母越说,这高二跑得越欢了。最后,祖母是彻底地高兴了,她对高二说:“高二,这光景不过了!你过来,我那板柜里有个白蒸馍,是过年敬灶火爷的时候,我偷偷藏下的,而今给你吃!算是奖赏你!”说罢,祖母从裤带上,解下个小钥匙给高二。
高二从板柜里取了馍。抱苞谷秆的时候,他顺便把这个馍拿来,让祖母煨在还冒着火星的麦秸灰里。待又一次抱苞谷秆回来的时候,这馍已经煨虚了,又虚又软又黄,热得烫手。
“你不要显能!躲在人背后吃!当心叫‘揽干手’给叼去了!”看着高二逞能的样子,祖母担心地说。“揽干手”是平原上的人对讨吃的的一种叫法。
手拿着这个馍,高二觉得自己如今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伟大的人物了。他一蹿蹿上了老崖,嘴里唱着歌谣,脚下踩着鼓点,摇头晃脑地一路走来。
这个馍他舍不得吃,一吃完他就又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可是不吃又抵挡不住这馍的诱惑。于是在踏歌而行中,他只把那馍放在嘴边,嗅了嗅它的香味,然后用指甲从馍上掐下黑豆粒大小的一点,放在嘴里嚼着。
顾兰子那红勾勾的眼睛也盯在那馍上,当两人擦身而过时,顾兰子也嗅到了馍那淡淡的麦香。不由自主地,或者说,下意识地,或者说,没有法子的事情,或者说,“我没有法子不这样做”,这六岁的孩子顾兰子,折回头,跟在那半大小子的后边。
第八章 顾兰子的第一次亮相(3)
所有的行路人都在麻木地走着,他们没有看到孩子反常的举动。包括女孩的父母也没有发现。
女孩尾随着那男孩子,踮着脚走屏住呼吸接近他,然后,斜马叉地蹿上去,一跃,从那男孩的手里抢过馍,立即转身,跑了起来。
那半大小子刚才把馍搭在嘴边时,他是决心把它吃掉了。但是还没容他吃,斜马叉地伸出一只手,抢走了这馍。半大小子有些发愣,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是空的,馍确实没有了。半大小子脑子“嗡”的一下,转过身去看,只见一个女孩子,红头绳扎着两个羊角辫,正向老崖那个方向跑。那女娃的手里,分明拿着他的馍。
半大小子回过头来去追。一边追一边口里仍不忘念口歌,不过这次的口歌内容变了,是这一带人给流浪的河南人编的:
河南担,打不烂,
打烂还是个河南担!
半大小子这样唱着。
顾兰子在前面跑着。她在奔跑的途中将那个对她的口来说有些过于大的馍往嘴里塞,但是跑得太急了,嘴里呼哧呼哧地又来不及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