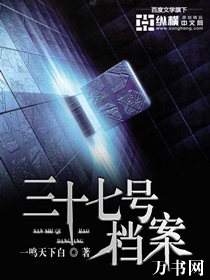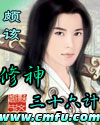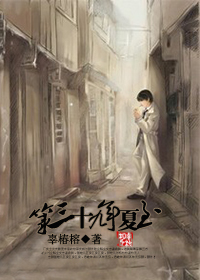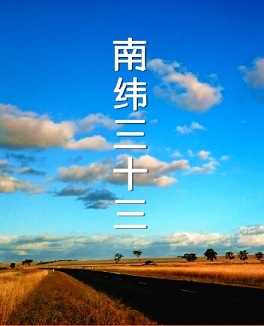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怎么办呢?你不来拿,我们就送去。
我们首先要送去的就是汉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汉语是“王”。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华民族古代和现代的智慧,也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国人要想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外国人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必须首先抓汉语。为了增强中外文化交流,为了加强中外人民的理解和友谊,我们首先必须抓汉语。因此,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首先送出去的也必须是汉语。
此外,汉语本身还具备一些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优点。5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八大翻译处的工作。在几个月的工作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现象,这就是:汉语是世界上最短的语言。使用汉语,能达到花费最少最少的劳动,传递最多最多的信息的目的。我们必须感谢我们的祖先,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汉语言文字这一瑰宝。过去的几千年,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仅就目前十几亿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人来说,他们在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方面所省出来的时间简直应该以天文数字来计算。汉语之为功可谓大矣。
从前听到有人说过,人造的世界语,不管叫什么名称,寿命都不会太长的。如果人类在未来真有一个世界语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语一定会是汉语的语法和英文的词汇。洋泾浜英语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说法虽然近乎畅想曲,近乎说笑话,但其中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说来说去,一句话: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这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意义。
2000年1月11日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1)
——读《丝绸之路》札记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巨著《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已由耿昇先生译为汉文。中国学人,懂英文者多,通法文者少。耿君此举,功德无量。
作者原籍伊朗,波斯文是他的母语,又精通*文及多种突厥系语言。他能直接使用用这些语言写成的典籍。这一点许多国家的学者都难以做到,我国学者也不例外。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读此书真如入宝山,到处是宝,拣不胜拣。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文中拣了一些宝。现在我专就中西文化差异这个主题,再写这一篇文章。
我先抄几段原书:
在*教初期,还流传着有关中国人的另一种传说:“中国是雅弗的后裔”,他们创造了大部分专门艺术(艾敏…艾哈迈德?拉齐:《七大洲世界》,约为公元1617—1618年)。根据这种在17世纪时还可以解释一种事实真相的传说认为,中国在工艺和技术方面都较西方民族发达,是中国发明了大部分艺术。在当代的欧洲,大家还认为是希腊创造了所有的艺术,“希腊奇迹”是官方教育中所热衷的内容。在波斯,大家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在承认希腊人于科学理论领域中无可争异(似应作“议”—羡林注)的功德的同时,却发现他们在技术领域中完全无能。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时代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论理(似应作“理论”——羡林注)。”
羡林按:这话说得似乎太绝对了一点,中国不能说没有一点科学理论。再接着抄:
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下面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扎希兹:《书简,论黑人较白人的优越性》)。这些作者们认为,这种观察证明了中国人(如同“*人”一样也属于有色人种)较希腊人、波斯人和“突厥人”(费尔干纳人,即锡尔河上游的塔吉克人)等民族(他们都是“白人”)的优越性。波斯国王哈桑(1453—1478年)也向威尼斯的使节约萨约?巴尔巴罗提到了这句谚语,但把“希腊人”译成了“法兰克人”。由于该使节非常欣赏波斯君主向他出示的中国产品,承认在威尼斯意大利都不能生产如此漂亮的东西。所以国王回答他说:“先生,当然如此。您当然知道这一句波斯谚语:中国人有两只眼,同时法兰克人则只有一只”〔《若萨法(羡林按:恐即上面的“约萨约”)?巴尔巴罗游记》,哈克鲁特出版社,1873年版,第58页〕。然而,意大利当时已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西方人在技术上的优势仅仅在18世纪初才成为事实。(页329)
下面再抄一段原书:
继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绸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吉希斯:《论有色人种较白人之优越性》)(页376)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2)
羡林按:这里讲的同上面讲的是一码事。所谓“吉希斯:《论有色人种较白人之优越性》”一书,实即上面的“扎希兹:《书简,论黑人较白人的优越性》”。译者一时疏忽,把著者译成几乎完全不同的名字,又误译“有色人种”为“黑人”。
但这不是我要研究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上面两段引文中所叙述的事实和谈到的说法,实有重大意义。到了今天,其意义更为突出。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个说法中实际上蕴含着一种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比较研究。我决不是由于古代的穆斯林,特别是波斯的穆斯林,说了中国的好话,而沾沾自喜,想同古希腊争一日之长,尽管在今日世界上“言必称希腊”的氛围中这个“一日之长”还是可以争一争的。我所说的“比较研究”,是指古代穆斯林们在中希文化的对比中所做的分析和观察,含有非常深的意义,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
在漫长的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一些不同的文化。每当两个文化相接触相撞击时,敏感的人们就能从中体会出、感觉出、观察出两个文化间的同或异,特别是差异,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要举这样的例子,是颇能举出一些来的。但是,我现在要探讨的范围仅限于以中国为一方的文化撞击。所以,我举例子,也只举这方面的例子。
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同外来文化的撞击,大大小小,为数颇多。但是,其中最大的仅有二次:一次是佛教输入,一次是西学东渐。这两次撞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贯串在自佛教传入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外来的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边撞击,边矛盾,边和解,边融合,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提高,外来文化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永远也不会结束。
佛教至迟到了汉代已经传入中国。尽管在最初它也做了一些姿态,甚至依附于鬼神方术,以期能在这一块陌生的土地上立定脚跟;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同中国文化的根本差异,敏感的人士不久就觉察到了。牟子《理惑论》援引世俗非难佛道的话说: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纪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言也。
佛教教义与中国文化其他差异也表现出来了。《理惑论》又说:
向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
甚至佛教最根本的教义之一:无我(Anātman)也有所流露。《四十二章经》说:
佛言,孰自念身中四大,名自有名,都为无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
“无吾”就是“无我”。此外,佛教还有一些行动规范,比如沙门不拜王者之类,都是与中国的传统的道德规范针锋相对的。佛教为一方,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和道家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中国古代儒释道的典籍中都能找到一些。具体的例子我不列举了。唐代高僧玄奘实际上也观察到了中印文化的差异,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我在这里只举一个平常不引起人们注意的小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唐太宗应天竺童子王(Kumāra)之请,让僧道协作,把《道德经》译为梵文,以流布五天竺。但是翻译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经中的“道”字怎样翻?道士们主张译为“菩提”,也就是梵文的bodhi,是佛家名词。玄奘以为不妥,坚持译为Mārga(末伽),梵文的意思是“道路”。双方争执,各不相让。《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详细地记载了这一件事。我从中选出关键性的一节,抄录如下: 。 想看书来
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3)
自此众锋一时潜退,便译尽文。河上序胤,缺而不出。成英曰:“老经幽秘,闻必具仪。非夫序胤,何以开悟?请为翻度,惠彼边戎。”奘曰:“观老存身存国之文,文词具矣。叩齿咽液之序,序实惊人。同巫觋之淫哇,等禽兽之浅术,将恐西关异国,有愧卿邦。”英等不惬其情,以事陈诸朝宰。中书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庄不?”答:“彼土尚道九十六家,并厌形骸为桎梏,指神我为圣本。莫不沦滞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练精灵,不能出俗。上极非想,终坠无间。至如顺俗四大之术,冥初(物)六谛之宗,东夏老庄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为笑林。奘告忠诚,如何不相体悉!”当时中书门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页387a—b)
从这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在体会到中印文化有差异的基础上,既贬抑了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的序,又贬抑了老庄本身。这是唐代佛道矛盾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到了宋代,高僧赞宁在他的《高僧传》,卷27,《含光传》后面,写了一个“系”。里面讲到佛教“倒传西域”的问题。他由此而讲到中国人和印度人著述体裁的差异,对待哲学宗教态度的差异,其基础也就是文化的差异。我引一段话:
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大正藏》,卷50,页879)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儿是“念性”和“解性”。对于这两个词儿,我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作了详尽的分析,请参阅。我在这里只笼统地解释几句。所谓“性”,在佛典中有很多含义。梵文的prakrti,svabhāva都能译为性。意思是“本体”、“自性”、“本质”,平常所说的“真如”,有时也等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