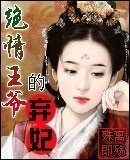祖师爷的儿媳妇-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在同一天,我烧掉那本书回到家里,再一次被震惊得呆掉了。家里就像遭了强盗一样,花花绿绿的糖果散落地上,墙上的挂画东倒西歪,鞋子被丢得东一只西一只,就连茶几上的电话也被摔得老远,听筒线胡乱地搅在一起。我呆呆地扶着门框,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母亲眼神呆滞地坐在地板上。她没有看我一眼,只是紧紧盯着面前的地板,久久才眨一下眼睛,一眨就落下一串眼泪。她的头发散落在肩膀上,半截裙子盖住她的腿。一双好看的脚裸'露在外面,两条腿被泛着青光的瓷质地板冻出一块淡淡的淤青。脸上有未干的泪渍,在灯光的反射下照出一片黯淡的光,我就在那片黯淡里看到了我同样黯淡的未来。
父亲就这样走了,带走了属于他的一切。他的奖章他的军装他的衬衣他的剃须刀,就连桌上三只一套的茶盅他都带走了他常用的那只,干净、彻底,就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他安静而平静地拿走了属于他的一切,而不属于他的——比如我,比如母亲,他一概不要。我像是忽然明白了那些昂贵的零食和温声笑语的含义,真是愚昧,愚昧!我愤愤然地起身,捡起地上的糖果丢出了家门。这还不够,我唾弃它的肮脏。我又跑到门口,将糖果都捡到衣兜里,带到了河岸对面的垃圾平原,再狠狠地踩进那千疮百孔的暗黑里。肮脏了的父爱,只配活在垃圾堆里。肮脏了的父亲,不配得到原谅。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但我的眼泪流了一路。
我再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还是坐在地板上。她像是失去了提线的木偶,眼神呆滞,毫无生气,一动不动。她再也没有看过我一眼。我抱着她,喊她,她都不应。她脸上的泪痕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她饱满的嘴唇已经皲裂,起了一层薄薄的白皮。她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几岁。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无声地反抗这一切,没有只言片语。我也那样看了她一天,没有只言片语,直到这一片沉寂被阿甘婶的破锣声搅碎了。
那是个身材肥硕的女人,一双大脚铿铿踩在地板上,有一种踏穿地板的气势。她一进门就开始呼天抢地,脸上挂着不知有多少真情的眼泪,粗鲁地推开家里每一扇门查看,连厕所都不放过,口中一直哭喊着父亲把他们家男人带坏了,带走了。她的男人,就叫阿甘,是个很憨实的男人,据说曾是父亲出生入死的兄弟,两人亲如手足,一起当兵,一起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在这里娶妻生子。他逢年过节都会来家里拜访,偶尔唠叨一下他这个没教养的查某和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还是大哥你好。”他总是唯唯诺诺地这样说,然后嘿嘿地憨笑,露出一排长期吸食烟酒的黄黄的牙齿。父亲通常只是弹着烟灰,没有回应。
阿甘婶聒噪的声音一直在继续,这出没有对白的独角戏她演得不亦乐乎。她说父亲是外省猪仔,联合起来欺负他们,占他们的地方,睡他们的查某,最后还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她说我们是粥锅里的老鼠屎,是害群之马。她站在母亲面前,居高临下地望着她,说她是红颜祸水,是狐狸精,是罪有应得。母亲没有抬一下眼皮,她像是聋哑了,什么都听不到看不到,任由着阿甘婶数落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为她出头,被阿甘婶推倒一边,她也不看一眼。门口挤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查某,还有三两个村公所的管事,但没有人为我们说话。叽叽喳喳地响着一些声音,我什么都听不清,只剩下一张张嘴在动。
围在外圈的男人肆无忌惮地盯着母亲。这是个深居简出的女人,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美人。据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有一堆男人上门求亲,但不知为何她最后竟选了父亲这个阿甘婶口中的外省猪仔。或许,曾经的父亲真的很英勇,在这个小小的镇上,也唯有他这样的男人才配得起她这样的美貌。般配如斯,他们本应该天长地久的,所以我一直都不能理解父亲为何那般决绝,母亲又如何此般淡然,难道父亲大陆的那个老婆比母亲更漂亮吗?直到很久以后,我又在父亲的书中看到了那张被撕成两半的黑白照片。照片已经发旧发黄,被人小心的粘合在一起。年代久远,依稀只能看见照片上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孩,一个小男孩拉着她的裤管,旁边站着一个年长的女人。照片上的女子,打扮得一点都不漂亮,可以说是非常庸俗,相貌更是不如母亲,但那个笑,温柔极了。那个眼神,在我的学识增加些许之后终于可以找到了一个词形容——含情脉脉,大概就是老婆的代名词吧,不是美丽或风情可比拟,而是一双眼中只有彼此的缱绻。这就是父亲心心念念的那个大陆的家,他的妻儿和母亲,于是他回到了那个我们在书本上叫做水深火热的地方。
一个女人的卑微莫过于此了,但这样的卑微却是她咎由自取。美丽的女人,在男人眼里就是一件奢侈的附属品,有她,也许会颜上增光,比如牙齿;没她,也是无关痛痒,比如盲肠。而母亲之于父亲,就是盲肠的意义。因为他的牙齿,在大陆。
母亲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抬一下眼皮。众人渐渐散去。在他们眼中,别人家的戏始终是茶余饭后的赏玩,哪里比得上回自己家给老公孩子做晚饭来得重要。
天黑透之后,阿甘回来了。他推开门进来,轻轻叫了一声“嫂子”,似乎终于把母亲的魂叫回来了。她缓缓地抬头,有几秒钟的时间,黯然失色的眼睛慢慢变得流光溢彩,就像经过寒冷的冬季慢慢吐春的草木,一眨眼便已春意盎然。母亲倏地从地上站起来,想要扑过去,但她整整坐了一天一夜的身子早已冻僵,麻木,没有知觉。阿甘扶着她到沙发上休息,但她不肯,蹒跚着走到门口,急急求证父亲是不是回来了。
“嫂子……”阿甘这样木讷地叫着,他的头低得很低,似乎很是愧疚。“他真的走了。”他说,“我亲自把他送上船的,我亲眼看着他走的。”
“我不信!”母亲忽地大喊起来,她的头发散落下来,看上去像个竭斯底里的疯子,她再也不是我那个温柔娴雅的母亲了。她的手紧紧揪着阿甘的手臂,“我不信,我不信他就这样走了。他是不是就在外面?他肯定在气我,气我说那个女人坏话。”她还要走出去,阿甘扶着她。门外早已漆黑一片,在杳杳冥冥的黑暗里,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冰凉的夜风四处流窜。
“嫂子,他真的走了。”他又小声地说。母亲终于沿着门框滑到了地面,泪流满面。母亲沉默了两天之后终于爆发,凄厉的哭声一直在房子里回荡。我想我也应该哭,心里莫名的悲痛压得我心口好疼,可我的泪腺像是干涸了。我身体里的战斗细胞却完全清醒了,我像打了鸡血一样冲上去,对阿甘拳打脚踢,让他还我父亲。阿甘没有制止我,只是一脸愧疚地看着母亲。不久,阿甘婶就来了,怒气冲冲地拉着他的胳膊死拉硬拽地拖走了。房子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夜渐渐静下来,我终于在沙发睡了过去。
那一年是一九七二年,我十岁,国小四年级。
☆、第 4 章
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父亲,十九岁的时候生下了我。父亲足足大了她一倍,她一辈子没吃过苦,没失去过依靠。父亲走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都处在混乱之中。母亲没有想过去工作,因为她什么都不会做。她会做饭,会洗碗,可她又放不下面子去饭馆里做这些杂活,每日便只是在房子里等我放学回来。开始的时候,阿甘还试图帮衬我们。所谓帮衬,也就是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悄悄地塞给我几块钱或一些小文具,但我始终记着他帮助父亲离开的事情,始终没给他过好脸色。那时候他因为父亲的事接受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调查,后来只得在村里的工厂上班。那是一家很小的机械零件加工厂,每次走近都能听到刺耳的钢铁切割声。从工厂里流出来的废水是黄色的,沿着那条村外的河延绵上千米,可想而知里面的工作环境多么恶劣。他说他在赎罪,书本上也教过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或许因为这件事,我终于原谅了他。
后来有一次他给了我五十块钱,那个时候,这些钱足够我和母亲一周的生活了,我便忍不住告诉了母亲,还谎称是路上捡来的,然而母亲一眼就拆穿了我这个拙劣的谎言。母亲听到我一直在受阿甘所谓的帮父亲照顾我们的话气得手指发颤,她戳着我的额头骂我不孝,是财奴、势利鬼、讨债鬼。她问我到底拿了阿甘多少钱,可我早已经记不得了。她气愤地从首饰盒里拿出一张百元甩在我脸上,问我够了没有,我连应都不敢应一声,她又甩了一张。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落了下来,我从未想过拿阿甘的钱是这么大的罪过。她走了之后我才敢颤栗栗地捡起那些钱。
我记得那是个黄昏,天似乎都跟着我哭了。我一路哭着一路紧紧地攥着那两张钱打算跑到阿甘家里兴师问罪,却只看到阿甘婶坐在门口择菜。
“阿甘呢?”我怒气冲冲地问。
她不屑地抬头瞥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择菜。
“阿甘呢?”我提高了音量。
“阿甘阿甘……”她喃喃重复道,“果然是有娘生没爹养的小杂种,就不知道个尊卑啊!”她骂得咬牙切齿,我心里的委屈和怒气倾泻而出,一下掀翻了她的菜篮子就跑开了,身后仍传来她中气十足的骂声:“小杂种!你别给我逮住。”
我跑着跑着脚步却慢慢停下来了。从来没有人当面这样骂过我,这么明目张胆,这么嚣张跋扈。而这个女人,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她每次见到我总是一副哈巴狗的模样舔着脸奉承我是天生丽质的小公主,若是父亲因此给她一些什么赏赐的话,她就会更卖命的夸奖。现在,还没多长时间,她就敢戳着我的脊梁骂我小杂种了。
我回过头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好菜篮子转身回屋了,嘴里依然还在念叨着什么。那一年,我十一岁,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只捡起一块石头冲着那肥墩墩的身子扔了过去然后没命地跑起来,一直跑到身边呼啦升腾起一片美丽的白鹭鸶,我才发觉已经跑到河岸对面的树林里了。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在树下休息了很久才缓过来,想着阿甘婶这回肯定不会放过我了,又想着母亲那张气得发青的脸,怎么也迈不动腿回家了。天渐渐暗下来,我手里还紧紧攥着准备还给阿甘此刻已被我蹂躏得皱皱巴巴的钱。我想这一切都是阿甘的错,要不是他,母亲不会那么气愤;要不是他,那个臭婆娘不会骂我小杂种;要不是他,我不会有家不能回。我越想越气愤,连心里那点害怕都顾不上了,只匆匆跑去找他算账。
后来我在路上截到了阿甘,我像母亲甩我钱一样把钱甩给他,正式和他恩断义绝。他缓缓地把那钱捡起来,也没有问我为什么。他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摆平了他老婆。那个唯唯诺诺又惧内的男人,终于有一次像个真正的男人了,不过也仅仅那么一次而已。那块石头到底没造成多大的伤害,阿甘一拍板断喝一声也就过去了。我因此得了个顽劣之名。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见到他。再见他的时候他的背似乎有些驼了,头发也花白了。他没有再帮衬我们任何事情,他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