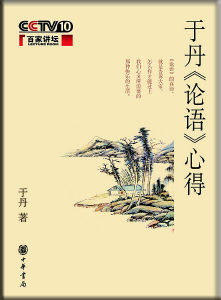于丹论语心得(百家讲坛丛书)-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家会看到,孔子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更谦逊,一个比一个更平和,一个比一个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终端的愿望。
在今天看来,一个人的发展,最重要的往往不在于终极的理想有多么高远,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我们往往不缺乏宏图伟志,而缺少通向那个志愿的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切实的道路。
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你想做什么呢?
曾皙名点。他没有立即说话,《论语》对此写得惟妙惟肖,叫做“鼓瑟希”,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原来刚才他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瑟,听到老师问自己,他让瑟声逐渐逐渐缓和下来,缓和到最后一声,“铿尔”,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我们熟悉的《琵琶行》所描写的那样,“曲终收拨当心画”,让乐曲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曾皙不慌不忙,“舍瑟而作”。什么是作呢?那个时候人们是席地而坐,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都是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当要回答老师的提问时,要站起来以表示恭敬,这就叫“作”。曾皙是把瑟放在一边,然后毕恭毕敬站起身来答对老师的问话。
从这样几个字的描写能够看出什么来呢?可以看出曾皙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不会像子路那样“率尔”而对,而是娓娓道来,成竹在胸。他先是征求老师的意见,说,我的理想和这三位同学不一样,能说吗?老师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要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嘛。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阐述他的理想。他说,我的理想是,到了暮春时节,就是阴历的三月,穿上新做的春装,在这个大地开化,万物复苏的季节,陪同几个成年的朋友,再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冻的沂水中,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沂水旁边的舞雩台上,沐着春风,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成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
孔子听了他的话,长长地感叹一声说:“吾与点也!”“与”,赞同。即是说,孔子的理想和曾点是一样的。这是四个学生畅谈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老师发表的唯一一句评价的话。
各人的理想谈完了,子路、冉有和公西华他们三个就下去了。曾皙没有立即出去,而是问老师,您觉得他们三个说得怎么样呢?
老师也很巧妙,他先挡了一下,没有作正面评价,说,无非是每个人说说自己的想法嘛。
但曾皙还要继续问老师,那为什么子路说完话您冷笑了一下呢?
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他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治理一个国家最核心的东西是讲究礼让,可是子路的话一点都不谦虚,所以笑笑他。意思是说,要以礼制去治理一个国家,首先你的内心要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一个起点。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发言,说明他内心缺乏一种恭敬和辞让啊。
接下来曾皙又问,难道冉有不是想治理一个国家吗?(您为什么没有哂笑他?)
老师说,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
曾皙又问,难道公西华说的不是治理国家吗?(怎么也没见您哂笑他?)
老师说,有宗庙,又有国际间的盟会,不是治理国家是什么?像他这样精通礼仪的人说想做一个小司仪者,那么谁又能做大司仪者呢?
孔子的意思是说,他笑子路,不是笑他没有治国理政的才干,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治理对象的大小,不在于它是不是国家,而在于自己的态度。因为冉有和公西华态度谦逊,而他们又有实际的才干,所以孔子没有哂笑他们。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孔子并没有否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理想,为什么唯独对曾皙给予热情鼓励呢?从孔子对曾皙的支持中,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此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读。他说,曾皙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四书集注》),好像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但是曾皙的内心是完满充盈的,他以自身人格的完善为前提,以万物各得其所为理想,这就比另外那三个人想从事一个具体的职业,在那个职业上做出成绩要高出一个层次。
这就是孔夫子说过的“君子不器”。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位为目的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的,他要从最近的、从内心的完善做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能让你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呢?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被遮蔽的恰恰是我们心灵的声音。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过得很不开心,觉得自己有抑郁症的前兆,就去看心理医生。
他跟医生讲,我每天特别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一回到家里就会感到惶惑。我不知道自己心里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越到晚上,我的心里面会越恐惧,越压抑,所以常常整夜失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一进入工作状态,我的症状就消失了。长此以往,我很害怕会得上抑郁症。
这个医生认真听完他的倾诉后,给了他一个建议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他的喜剧演得好极了,所有人看了以后都会开怀大笑,忘怀得失。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的演出?等看上一段时间后,我们再聊一聊,看你这种抑郁症前兆是不是有所缓解,然后我们再来商量方案。
听完医生的话,这个人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看着医生的时候,已经是满面泪水。他艰难地对医生说,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
这好像是一个寓言,但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角色,在角色中欢欣地表演,认为这就是自己的理想,这就是成功的职业,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心灵的愿望受到尊重呢?我们在角色之外,还留有多大的空间,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呢?这就是很多人离开职业角色之后,反而觉得仓惶失措的根源所在。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做着过冬准备。
第一只田鼠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搬进洞里。
第二只田鼠卖力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稻草、棉絮拖进洞里。
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
那两个伙伴一边忙活,一边指责第三只田鼠说,你这么懒惰,也不为过冬做准备,看你到了冬天怎么办!
这只田鼠也不辩解。
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躲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洞里面,看着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每天无所事事。渐渐地,大家觉得非常无聊,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些时光。
在这个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另两只田鼠讲故事。比如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它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看到他在做什么什么;又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它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什么;它说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曾经听到鸟儿在唱一种歌谣……
它的那两个伙伴这才知道,这只田鼠当时是在为大家储备过冬的阳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曾皙的理想,他在大地开冻、万物欣欣向荣的时节,安排一个洗涤自己、亲近自然的仪式,这个仪式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的意义,但是它却能给内心一个安顿。这种安顿需要我们与天地合一,去敏锐地感知自然节序的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人来讲是特别奢侈了。在现代化的今天,反季节的事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当生活的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四季走过的痕迹,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什么四季分明,什么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已经激不起什么反响。我们不会像曾皙那样敏感,想到在暮春时节,让自己去受一次心灵的陶冶,从而把自己更大的理想,坚定地放飞出去。
理想和行动的关系,就如同引线和风筝的关系。这个风筝能飞多远,关键在于你手中的线。而这条线,就是你的内心愿望。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这会使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担当,能够做到最好。
许多人感到,《侍坐》这样一章阐述的理想似乎不同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论语》关于立志的判读,不同于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那样的沉重。但是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它却是所有那些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在《论语》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学生子贡去问老师:“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
老师告诉他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约束,内心有坚定的不妥协的做人标准;同时这个人要对社会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以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你要忠于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啊。所以这是孔子说的“士”的最高标准。
子贡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低一些的标准啊?
孔子回答他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宗族称赞他孝敬父母,乡里称赞他恭敬尊长。你能够从身边做起,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这种爱的力量去得到周边人的认可,不辱祖先,这就是次一等的“士”。
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更下一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