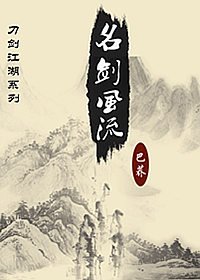风流相公西门庆-第2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皇城司两位勾当官今天都在这里;张如晦;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言。”
钱贵罕见的厉声道:“你那个皇城使的头衔在老夫看来;就是个屁!”
说完钱贵又转头笑眯眯的问道:“谭大人;你说呢?”
谭稹如果说“是”;便承认皇城使是个屁;如果说“不是”;便又显得和钱贵意见不合。
“这老狐狸;把自己拉出来原来是为了这个!”
谭稹暗骂一声;想了想道:“张道长也是古道热肠;一时失言而已;钱大人何必动怒?”
钱贵点点头:“你们继续!”拉着谭稹又回屋去了;留下目瞪口呆的众人。
西门庆呵呵笑道:“张道长;皇城使不是拿来开玩笑的;你还是好好珍惜吧。”
第二百七十九章无情打脸
张如晦面sè十分的jīng彩;本来这些都是和梁乐等人串通好的;但千算万算没想到钱贵也会来到这里;更没想到的是钱贵这个老狐狸居然拉了谭稹一起来。
两位勾当官齐齐现身;当面驳斥他的说法;做人做到这份上;真是恨不能跺开一条地缝钻进去了。
“贫道。告辞!”张如晦含糊的说了一句;就果断闪人了。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
张如晦这一撤;把梁乐晾在了当场;西门庆有些玩味的目光扫过来;让梁乐忍不住从心底发寒。
西门庆什么时候得到皇城司两名勾当官的支持了?
“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妾潘氏没有拿到酿酒权?”西门庆笑着问道:“梁楼主;做人要厚道;你突然发飙;质问本官;是何道理?更是在本官今天大办婚事、众目睽睽之下;让本官。很难办啊?”
“梁楼主;你是让本官记仇呢。记仇呢。还是记仇呢?”
西门庆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唯一没有发笑的就是梁乐还是那些正店掌柜们。
“大人有大量;不过梁某不明白的是。”梁乐咬咬牙;继续硬挺:“为何我们三十六家正店都没有收到官府公文通知?”
“潘氏拿到酿酒权;有何人可作证?”
梁乐这话还没说完;门口就有人接口道:“自有本王作证;你可有意见?”
“原来是嘉王到了!”西门庆大喜;急忙上前迎接;只见嘉王身矗服;身边有位中年人;后面两个黄门官跟着。
梁乐一见这中年人;便惊出一身汗来;不知不觉中已经瘫坐在椅子上。
嘉王他不认得;但这中年人便是开封府的酒务王铠;每年酿酒权都是由此人核定;梁乐怎么会不认识?
嘉王说完这一句后;并未理睬梁乐;而是笑对西门庆道:“你今天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啊!”
“下官谢过王爷!”西门庆上前行礼:“楼上雅间已然备好;王爷还请上楼品一品这吹雪楼的酒菜如何?”
嘉王赵楷摆摆手道:“不急;先把事情了了。”说的向旁边那王铠示意道:“你来给那些不长眼的说说。”
王铠上前半步;咳嗽一声;目光扫过全场;那些正店掌柜们顿时低下了头;得罪了酒务大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有了酿酒权;每年的收益可就没了很大一块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已经非常后悔加入这一伙;和梁乐坐在一起了。
“某是开封府酒务王铠;潘氏经营的吹雪楼已经取得酿酒权;为汴梁第三十七家正店!”
当场鸦雀无声;嘉王赵楷接着道:“本王今天来是凑个热闹;没想到有人居然乘机捣乱;这种行为恐怕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能做出来的。另外;本王还要宣布一件事情。”
“那就是从今rì起;西门指挥使已然升任皇城司勾当官!”
说着赵楷一挥手;后面黄门官送上诏书;西门庆肃然行礼;伸手接过:“王爷;王大人;楼上请!”
“好!本王今天就要尝尝吹雪楼的手艺。”赵楷说完突然低声问道:“西门勾当;你那两个刚过门的小妾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罢?吵架没有?”
西门庆听了莞尔一笑;知道赵楷少年心xìng;开了盘口不说居然还想作弊;从自己这个当事人口中套取第一手情报。
当下西门庆微笑道:“王爷;下官也投了一百贯的;赌的是全家和睦。”
“哦?”赵楷笑道:“本王也相信西门勾当本事不小;自己家里这点事情自然能摆的平。”
“那王爷赌的是。?”
“本王是庄家;不参赌。”赵楷微微一笑:“走;上去和钱勾当、谭勾当聊聊皇城司以后的事情;那个指挥是时候补充人员进来了。”
“关于这一点;下官也有些想法。”
西门庆一行上楼之后;只留下梁乐在座位上气得发抖;其他正店掌柜们一个个都像雨打的芭蕉雷击的蛤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梁乐断然起身;拂袖而去;这地方再呆下去只会丢脸而已;梁乐这一走;其他正店掌柜们也如坐针毡般的呆不住;一个个跑了;顿时空了两三张桌子出来。
岳飞见了哈哈大笑;引得其他人都笑起来;那些正店掌柜们顿觉颜面全无;本来是跟着梁乐看好戏的;没想到好戏是有的;但主角却是自己这些人!
“老胡;梁楼主看来是靠不住了;我们怎么办?”走出吹雪楼;有掌柜的忍不住问道。
那胡掌柜摸着下巴道:“怎么办?当然是要重新选个领头的出来才行;照这样下去;迟早被梁乐害死!”
“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去备礼物;明天好好送到这儿;真心实意祝贺吹雪楼开业!”
。
。
酒席一直持续到月上中天才散去;等嘉王和钱贵、谭稹走了;西门庆才打开诏令看了看;这里面不但是任命自己为勾当官;而且武松也如同所料一般;转成指挥使了。
方才西门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嘉王的首肯;虽然谭稹颇有微词;但招收破落户进皇城司至少要过好几道考核才行;倒也打消了他的顾虑。
考核不通过的话;就怪不得别人了!
按照西门庆的想法;至少自己这些吹雪亲兵队是没有问题的;破落户里面也多有好手;再加上从其他四个指挥使中匀出的老成察子;这个新指挥人员补充起来还真是没啥难度。
关于大牢里的通事局探子马肃;嘉王倒是不置可否;对于他来说;只是蚂蚁一般的人物;死活倒也没什么;三位勾当官商量了一阵之后;还是决定先继续囚禁起来;视刺探犬的训练是否顺利而定。
虽然秦飞用非常手段让马肃吐露出不少东西;这里面就包括刺探犬的训练方法;但真假还不知道;最害怕的不是假;而是大部分真货里面掺了几条假内容;关键时候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另外;鼓上蚤时迁做了皇城司的副指挥使;主要负责试着训练处第一批刺探犬来。
家中那条刺探犬“旺财”已经在后院寻了个僻静所在养了;几乎快成了宠物;西门庆对此情况也是无可奈何。
那些青楼勾栏的老鸨们被请来就觉得非常奇怪;不过这种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毕竟可以顺便“发展”新客户;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有回礼。
每人两小瓶加料的景阳chūn之外;还有一样东西。
一个沉甸甸的木盒。
里面装的是麻将;还附有详细说明;连同规则等等。
对此西门庆声称是自己闲暇时发明的一种类似于牌九的东西;可供消遣。
要想让麻将流行开来;自然是要增加曝光率;而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些勾栏青楼;对于这一点西门庆毫不怀疑。
鱼饵已下;就等着收网了!
虽然这一天下来疲惫的不行;回到家后西门庆还是把潘金莲和雪儿二女哄上了那张超级大床;折腾了一更光景才左搂右抱的睡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些礼节实在是繁琐;好在没有女方亲戚;潘金莲和雪儿、孙二娘都昨天就累得半死;还没歇过劲来;所以干脆就都顺着西门庆和武松的意思;统统取消了。
吹雪楼开业是在中午的时候;那续子听说了昨天梁乐的“表现”;一个个哪儿还有别的想法?所以西门庆和潘金莲等人一出现在吹雪楼;上来表忠心的一个接一个的;让西门庆有些厌烦了。
“好好安心做事;来这套做什么!”
听了东家的呵斥;这续子反而欢喜;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下去加力忙乎自己那摊子事情。
才赶走了厨子;伙计报来:“有其他正店掌柜的在门口等候;说是来祝贺吹雪楼开业。”
“哦?上前面看看!”西门庆招呼一声;和蒋敬来前面看时;好些个熟面孔。
打头的是那胡掌柜;要不是胖;都快要把头扎进泥里去了:“见过勾当官大人!”
紧接着从伙计手中取过礼单;恭恭敬敬双手呈到西门庆鼻子底下:“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西门庆并没有伸手去接;反而皱眉道:“本官身为皇城使勾当官;怎么可能收冗赂?以本官看;你们昨天送的酒什么的就挺好。”
“岂敢岂敢。”胡掌柜胖胖的脸上已经有些见汗:“吹雪楼开业;这是同行之间的贺礼;怎么是贿赂呢?”
说着转头看看其他正店掌柜的:“你们说是不是?”
昨天彻夜商议;这胡掌柜明显已经被大部分人认可;临时取代了丰乐楼梁乐;所以他一开口;其他正店掌柜的就异口同声的附和起来:“是贺礼;不是贿赂。”
“既然如此;那蒋先生你就统计下。”西门庆不耐烦的打了个哈欠:“诸位;这是吹雪楼的账房先生;礼单都交给他就行。”
话音未落;一旁神算子蒋敬就被那些人给围上来;手里、怀里、袖里被塞的到处都是。
西门庆见了哈哈大笑;命人取来长竹竿;拿过来轻轻一挑;遮挡的青布顿时落地;露出那两个大大的金字来。
便是当朝蔡太师亲笔所书的“吹雪”二字!
“吹雪楼;开业!”
第二百八十章密谋
几乎在同一时间;装着秦力首级的木头匣子被放到了谭稹的桌子上;一起到达的还有已经僵硬的乙组七号。
从怀州到东京汴梁约莫是四五百里路;秦飞带着乙组那些黑衣察子一路飞驰;几乎是一个昼夜赶到;也算是非常快了。
秦飞站到谭稹面前的时候;还在微微喘气。
换马不换人!
要不是秦飞果断干掉乙组七号;那些乙组的黑衣察子也未必这么听话。
“你做的很好。”谭稹拨开匣子里面首级上的凌乱白发;仔细看了看:“秦力总算伏诛;再也没有人可以质疑你的出身。”
“但本官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要杀死乙组七号。”谭稹伸手一指木板上那句僵硬的尸身:“本官让乙组七号跟你一起去的目的;就是要管束那些乙组的察子;你却把他杀了。”
“乙组七号不停下官号令;吐露下官的身份;不杀他不足以立威。”秦飞说起来和杀了只小鸡没什么区别;但语气中的寒意显然可辨:“大人手下的乙组察子首次随下官办事;搞出这种事情来;也并非是下官所愿。事已至此;还望大人降罪。”
谭稹突然笑道:“不。你做的很好;本官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事情只要搞清楚了就行;以后本官还要依仗秦指挥使做很多事情。”
“大人尽管吩咐。”秦飞拱手道:“秦飞定然竭尽全力。”
谭稹站起身来;在屋内绕着秦飞踱了两步;秦飞并未回头;而是神态自若的保持着刚才的姿态;但秦飞明显能感觉到谭稹的目光在审视着自己;似乎在琢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