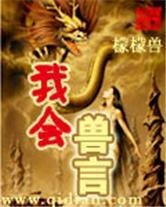姑妄言-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杏,自然是桃贵似杏。该她占先。”夭桃笑道:“人开口便说驴马,难道驴强似马么?我偏不让他。”夭桃笑道:“急来,我就让你先。只要二爷有个乘除加减,就在里头了。”姚泽民笑着就把红杏弄起,弄得他丢了,然后弄夭桃,足弄有二分工夫还久方歇。红杏道:“一样的人,你怎么偏心两样待?”姚泽民笑道:“一点不偏,你得头筹,他得后趣,可不是一样?”红杏道:“既这样说,下次再弄,我先让桃姐,我也照样要多弄一会的。”夭桃笑道:“你怎么比得我,人说桃饱杏伤人,桃多一些无妨,杏子自然该少些的。”大家顽笑了多时,方才散去。
过后姚泽民想道:“八人我已得六,那两个肯放过她们?须得设一网打尽之计方妙。时常在秋院中去走踅。那桂姨、菊姐也耳有所闻,知她姐妹皆已得了姚泽民,心中何尝不急。要屈身俯就,又恐被他看得下贱。要等他来垂青,又不见他动手动脚,猜测不知何意。疑道:”定是我两个容貌不如他们,所以他不来亲近,不然八个人中为何单弃我两个?他既无心到我,我去就他也是无益。“一腔醋气填塞在内,后来见了姚泽民,由不得怒气勃勃,那脸上竟像刮得下霜来一般。姚泽民见颜色正厉,越发连戏话都不敢说。孰不知她们色厉而内荏,故此倒日远日疏了。
一日,姚泽民偶然到她那里来。见红叶丫头在一张醉翁椅上睡觉,两足搁在椅轴上,两腿大楂,由不得失笑。左右张得没人,轻轻上前,将她衣裙掀起。自己取出肉具,扑她身上,一把抱住,将阳物隔着裤子混戳。红叶惊醒,说道:“还不放我起来。姨娘心里不好,在屋里睡着呢,看她起来看见。”姚泽民哪里听她,只是乱戳。那丫头被她戳得春兴大发,笑说道:“冒失鬼,这隔着裤子也是弄得进去的么?”姚泽民也不暇替她脱裤,双手将裤裆一撕,扯了一个大口子,就弄起来。那丫头搂着他的腰弄了一会,说道:“你歇了罢,看菊姐回来撞见,不说你这没廉耻的来寻我,还当我骚发了寻了你来的呢。”
正说着,鸡冠丫头蓦地走来看见,笑道:“没廉耻的,大白日里,你两个怎就链在一块儿了。”姚泽民连忙拔出,搂着鸡冠亲了个嘴,将她按在一张杌子上爬着,扯下裤子,露出光臀,就后边弄了进去,不住乱捣。红叶笑问道:“菊姨呢?”鸡冠颤着声儿道:“菊,菊姐还同夫,夫人下棋呢。我,我来家走走,不想遇了这活强盗,拿着我这样。”姚泽民笑道:“不要屈着你,你既不愿,就不弄罢。”鸡冠扭回头笑道:“你好自在话儿,我既被你强奸了,弄得我不受用,还不饶你呢。”两个笑着弄了好一会,方才住了。又同红叶复了一帐,恐菊姐回来,只得歇手。
姚泽民悄悄问红叶道:“你姨娘害什么病?”红叶道:“谁知道?她这两日茶饭也不大吃,口里只是叹气,夜里叫我替她做伴,翻来覆去,总不肯睡。熬得我要死,你不见我才在这里舂盹么?”姚泽民道:“大约是春心发了,想个人弄弄的意思。”红叶道:“她虽说不出口,大约此时有个趣人儿,她也未必辞。你何不去替她医医病?”姚泽民道:“我何尝不想她。她看见了我,那哭丧脸难看,不敢动手。”红叶笑道:“你做梦呢。她知道你同那三个姨娘三个姐姐相厚久了,她恼你不来亲近她。你若去陪个小心,包你成就好事了。”姚泽民方才恍然大悟,她原来因此而怒。鸡冠道:“你这没良心的,也怪不得她们恼。我菊姐虽不曾同你有什私事,她待你的情也算亲厚得很了,你有了别人倒撇了她,她恨不得咬你的肉呢。我听她的口声,口中虽说恨,心里还有几分恋你。你若同姨娘上了手,她自然也是肯的。”
姚泽民心中暗喜,走进房中,到床前一看,见她面朝里睡着,就坐在床沿上低低叫道:“姨娘,你身上哪里不好?我来问安了。”那桂姨明醒着,也不答应。姚泽民伸手去抚摸她身上,又问了一声。她忽然一个翻身,鼻中冷笑道:“你到你那些心坎上的人跟前去罢了,你来问我的是什么?空劳了你的心。”姚泽民道:“我听得你身上欠安,我心里急得了不得,忙来问候。一团好意,有什么心上人、心下人的。”她又冷笑道:“你当我不知道么?她们六个都是你心上的人,我两个你看不上眼,是你心下弃了的。你此时冷锅里豆儿炸,来说鬼话当什么。我几次要来拿你们的奸,一来怕带累你,二来姐妹一场,不好意思。她们虽瞒着我,宁叫她们不仁,不可我无义。两次三番,忍耐住了。论起来,都是一样的人,砖儿何厚,瓦儿何薄?就是我生得丑些,也不到怎么东施、嫫母的样子,你就这样分得清?”说着,就鸣鸣的哭起来了。姚泽民忙扯衫袖替她拭泪,她把脸又转了过去,用手推道:“你去罢,不稀罕你这虚情假意。”姚泽民忙跪在床下叩头,道:“要有一点假心者,就天诛地灭。我巴不得来亲近你,因见你见了我那气狠狠的脸嘴,我不敢放胆。若知你有这好情,我早来陪伴你了。是你自己耽误了好事,如何反怪我?”嘴里说着,就伸手去扯她的裤子。她忙攥着,道:“不要屈着你的心,你还去寻你的情人。”姚泽民道:“我的娘,我这样说,你还不信,你若不肯,我今日死在这里也不去了。”一面说着,忙自己脱了裤子,强将双手去解她裤带。桂姨还要做作,被姚泽民一下将她身子扳正,就伏上身。将铁硬的阳物,向胯中乱捣。桂姨情动,不能自持,手由不得放松了些,被他乘势脱下,弄了进去,抽扯起来。
弄过一度之后,桂姨说道:“你这坏人,我今日依了你,你后来定不稀罕我的。”姚泽民道:“我的娘,你不要讲这句话,屈死了人。若论模样,八个人中算你第一,要说风流,也算你第一,我心爱你久了。我要有一句谎言,促死、促灾。”桂姨此时方有了个笑脸,搂着他道:“你果有真心到我,菊姐不消说是你受用,红叶、鸡冠也凭你取乐。我们都是一样的姐妹,我难道要抢她们的先不成?要你一个公平心就罢了。若偏了我,我打听出来,却也不肯与你干休。”姚泽民道:“蒙你这样见爱,我还敢欺你么?她们六个派定一日一轮,今承你不弃,我若偏向你,怕她们争讲,也是挨此轮流就是了。”说着,将她臀儿垫起,两足挟于肋下,这一场弄,足有千余,把桂姨弄得四肢瘫软,喘息了一会。笑说道:“冤家,你有这样本事,怪不得人人爱你。我虽来了这几年,今日才知这件东西有如此妙处。”又笑道:“她们姐妹是谁先得起?”姚泽民将先后原委细细告诉她,桂姨笑道:“好个穿花蛱蝶,众人的花心都被你采了。”
二人正在说笑,听得菊姐回来了。桂姨道:“菊妹子,你来我同你说话。”那菊姐走到床前,见姚泽民在床上,便道:“这样没良心的人,姐姐容他来做什么?”就要走。原来这菊姐更风流更骚浪,当日同姚泽民顽笑,把臂捏腕,搂颈接唇,都是有的。只不曾沾在一处。后来因闻他有了众妇人,且又见桂姨正帅不能到手,那副将焉能得,就渐渐疏淡。菊姐满怀醋念,不能发泄。此时心中虽暗喜,但她醋意蓄久了,故有此话。桂姨接她坐下,道:“我方才也骂他没良心,他说因这些时你我见了他恼嘟嘟的,不知我们是什么意思,故此不敢放胆。是我们自己耽误了好事,据我说,也怪不得他。原是我们多心自误。”自替姚泽民游说了一番,才劝她上床。菊姐也就半推半就,同他做了于飞之乐。自此以后,姚华胄的这八妾八婢,他虚耽其名,姚泽民实受其惠。
一日,姚泽民想道:“她们众人都已到手了,料道不怕泄露。但常老婆她系夫人心爱的人,又在老爹跟前传话。况她素常长舌,若露了风声,如何了得?须得连她弄上,方才妥当。每日留心看机会。一日,远远见常氏在牡丹台畔小解,他悄悄走近前,一把抱住。他两个时常也戏谑惯了的,常氏又是个极淫之物,竟逆来顺受了他,也就两人见了一见大意。此后姚泽民方放了心,且搁过一边。
那时四海奠宏,万民乐业,治极生乱。到了天启三年,四川、广西就有些流贼勾引土苗倡乱,也不曾占据城池,只抢掳些人畜,杀了些老幼是有的。此时若有守城好将官领些兵去,这几个毛贼也就可以杀跑了。只因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忽闻得这个信,州县官惊得手足无措,便轻事重报:某处反了,凶猛异常。这些上司一见此报,生怕就杀到他跟前。功名性命还是小事,若把这些宦囊姬妾抢了去,将来儿子拿什么享用?也不查问有多少贼,据了何地方,便慌慌张张上本请兵,说得好不利害。天启见了本章,也恐地方有失,着九卿科道会议,命将出师。众人荐举姚华胄老将知兵,推他去征剿。他此时已七十多岁了,他自己说了几十年大话,今日如何推老了去不得?倒是天启恐他年迈,受不得这烟瘴地方的苦楚,疑问众臣。众臣奏道:“昔日之廉颇、班超、赵充国、郭子仪、马援,皆系老将,故能成功。况且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姚华胄虽过七旬,矍铄犹如壮年,必能平贼。”天启遂命他领了兵去。那两处不过是些小土寇,闻得官兵到来,潜伏的潜伏,逃散的逃散,兵不血刃,地方已靖。他也竟妄自居功,报说一到就烽烟尽灭。天启在喜,大加赏赍。恐兵一撤回,贼又复起,就封他为镇西将军,驻镇广西。
那姚华胄出兵去后,他这位继夫人裘氏正在妙龄,嫁了恁个白头皓须、软如棉、浓如涕的老儿,心中之苦说不出来。每每见了姚泽民,便眼中冒火,想道:“我正是他的对子,怎这月下老人错把红丝系在他老子的足上?我一朵嫩蕊娇花,怎被这枯藤老树缠着?天公虽然错配,人力尚可挽回,何不把这儿子设法弄来孝敬我?”但有继母之尊,难以开口。且这老儿日日守着,也无空隙可乘。没奈何,只得忍住。无奈那不知趣的老儿还假卖风流,说情说趣,乃至引得春心举发起来,他又一点正事也干不得,间或就强而后可,软叮当的一个物件,又没处寻这么个小篾片帮扶他进去,弄得不疼不痒,更觉难过。往往欲火炽将起来,只好把那凉茶冷水往下咽,靠她灵犀一点来浇息了这火,万不能够。倒巴不得离开了他,孤眠独宿,眼不见为净,还略好捱些。死捱了几年,见他去了,如拔了眼中钉一般,心下倒觉得一爽。无奈那姚泽民每日在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见了他,心头小鹿就乱跳,脐下那件作怪的东西不由得一吸一吸的难过。心中暗想:“料道熬不过去,迟早总是放不掉他的,不如早一刻以救一刻之急。”每每要算计同他比翼鹣鹣,共偕连理,做那风流乐事。一则不得其由,二则难以启齿。那姚泽民虽有十分慕她的心,她有继母之尊,比众妾不同,连戏话也不敢乱说,怎敢轻易乱做?二人虽都有心,却不能觌面相诉。
裘氏一日正在兀坐踌躇,忽听得两个丫头拌嘴,一个叫春花,一个名秋月。听那秋月道:“你说我浪?你同二爷调情亲嘴,他伸手在你裤裆里,是我亲眼见的,那倒不是浪么?”春花道:“你也撇不得清,也不是什么清净姑姑儿。我见他那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