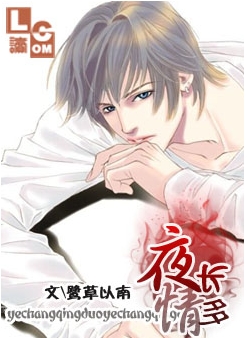滨海夜长风bl-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转眼间,季然二十四岁的生日,也在这漫漫的时间长河中悄然而过了,肖镇除了满怀欣喜地送他礼物,也怎么都掩饰不住一腔的担忧和着急。肖镇知道无计可施,不能逼,不能迫,不能求,也不能威胁。
肖镇学会了不再与季然争吵,学会了和谐共处,学会了怎样去爱,却学不会如何留住他逐渐枯萎的生命。
肖镇总是从后面拥住季然,二人在海边一坐就是一夜,从石滩到沙滩,他们给小山取名叫海角,而那宽广的水天相接的堤坝处,取名叫天涯。肖镇总是在发问,季然也总是在回答,肖镇想要去了解更多,更深,更细,关于季然的一切,他都想知道,他不想去忘记,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美丽的人,这样波澜壮阔地闯入了他的生命里。
终于,在季然再度昏昏沉沉睡过一个月醒来后,他第一次看到肖镇没有带着忧愁不堪以及痛苦满载的脸,季然对他微微一笑,肖镇也用朝他微笑点头。季然知道,自己当初爱上的那个大男孩长大了,不再那么冲动,取而代之的都是坚强,季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使命都将临近结束,这如烟花般的生命啊,曾经因为肖镇的天真而照亮了自己长久的夜,也曾因为肖镇的固执和善良让自己终能坦然微笑地走向死亡。
季然辞退了所有的工作,当然肖镇也不希望他再费力劳神什么,肖镇白日忙于工作,晚上抽空陪着季然,而肖镇也明白,此刻他拼命想握住的手,拼命想保护的人,正如那被海浪卷起推到岸边的细沙,又在下一阵海浪到来后,就会被轻易带走。
季然由每天昏睡12小时渐渐延长成18小时,季然的双眼已经由之前黄昏可以活动变成只能全黑才能行动,任何与阳光有关的一丝一毫,都能轻易地将他打倒。肖镇和季然似乎都有一种默契,那就是谁也不提他的病,除了大量的营养药物的服用,肖镇并无他法来抓住手中快要被风带走的细沙。
“我的生命如此短暂,我哪里还有时间去痛苦?”季然在日记里这样写到,他总是悄悄的写,然后将本子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那里记载着所有与肖镇发生的事,是快乐,是难过,是患难与共,还是不离不弃,是一切,却不是镜花水月。
季然的衰弱比肖镇想象的要快的更多,那句“他或许活不过二十五”总是将浅眠的肖镇从噩梦中唤醒,而他也总是俯下身去,静静地听身边人的呼吸声,在确定身边的人没有消失而去之后,他才能再度入睡。
肖镇买回欧式烛台,关闭窗帘成为他的习惯之一,让季然宽慰和心痛的是,至始至终,肖镇始终没有抱怨过一个字。
他们聊了很多,也终于将话题说到了季叙风的头上。肖镇最终向季然坦白了自己看都的一切,而季然说:“如果我的取走我一个肾,还能再换他几年生命,我可以把另外一个留下来给他。”
当时肖镇拥住他的手臂就在发着抖,他不想再多说,只是将季然抱得很紧,“季然,你恨他吗?”
“我只知道,我母亲很爱很爱他,她从未恨过他,而我也希望他能活得好。”季然并未计较太多。
“是么……”是啊。就连他的亲生儿子都不计较,我肖镇还能说什么?
“肖镇,我们初遇那会,你总说清高不能当饭吃。”季然说道,肖镇知道他又开始使他的小坏,带点小欺负。
“季然,清高现在也不能当饭吃。”肖镇郑重其事。
“肖镇你没听过精神粮食吗?人不喝水,会渴死,不吃饭,会饿死,人若少了精神粮食,那就……会空虚死。”季然如此解释。
“嗯……好吧,算你有点道理。季然,你知道我为何总比作你是神仙吗?”肖镇笑嘻嘻地问。
“呵,你这人奇怪呗,还能有什么解释?”季然晃了晃脑袋,得意地说。
“因为呐,季然,神仙不懂去恨,就算被凡人所伤,也不会去恨凡人的。”肖镇如是说道。
有时候他们驾游船出海捕鱼,有时候就爬上天涯山,带上一份自制沙拉,看着滨海镇美不胜收的夜景,更多的时候,其实还是肖镇盯着床上一动不动的人死死地看,他怎么也看不厌,也无法想象那人最终消失后,将留给自己多少孤独。
肖镇拒绝了一切来访,甚至母亲,好友……罗姨和段科偶尔会前来,只道他们过得好,也很少来打扰,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日子渐渐近了,这美梦,终要醒了。
第三十四话 冷夜恩仇
季然生辰的前二个月。
“肖镇呀,”季然陷在沙发中,看着电视里的卡通,“带我去看看季叙风吧!”
正在盥洗室里刷着牙的肖镇忽然停住,他一口吐掉满口泡沫,皱紧了眉头,什么!
“季然……你确定吗?”
季然点了点头,他端起昨夜未品尝完的龙舌兰,轻轻抿了一口,“是啊,为什么不呢,我的亲人……”
“季然,你一点都不恨他?”肖镇追问,他曾经那样对待你们母子,而十年后,伤害仍旧没有停止,甚至连我们无法长相厮守,也跟他当年的罪行脱不了干系。
“不恨啊,又什么好去恨?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珍宝,我比他幸运多啦。”季然看着肖镇脸上还挂着泡沫,便指了指。
肖镇又回去盥洗室对着镜子洗起来,一边问道,“季然,其实我手中抓了他好多辫子,随时让他身败名裂,就算我没他辫子我都能给他做几个出来,哼!”肖镇一边擦着脸一边走了出来。
“啧啧,肖镇你外表纯洁,没想到你整人还有高招啊?”
“开什么玩笑,人在江湖飘,怎能没高招啊!”肖镇从季然手中夺过那未完的酒杯,一口饮尽,“你刚才说最大的珍宝是什么?”
“呵呵……”季然将手抱住枕在脑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肖镇,“自然是你啊。”
于是没有季然免疫力的肖镇瞬间红了脸。
“肖镇,我很爱你。每日只想做一些平凡简单的事,烧菜,做点心,一起逛超市,爬山,看海……”
“我也是……”肖镇目不转睛地望着季然,“季然我终于懂得为何你当初要叫那部T3为 normal; normal life; normal happiness……我都知道。”
“嗯”季然点点头,“你愿意一生一世都陪着我平凡吗?肖大名人?”
“好吧,季然,我承认我每每给你一点阳光,你就会极度灿烂,我……”肖镇想说我当然会陪你一生一世,却不料心理一阵无以言状的难过涌起,他顿了顿,“季然,我愿意生生世世都陪你,我一直相信我们将会有下一次生命,下一次的相遇,不管你变成什么,我都会再次找到你。”
“呃……要是我变成大海星呢?”季然来了兴趣。
“那我就是珊瑚。”
“好吧,如果我成了巨大的岩石呢?”
“你难道没听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一说吗?”肖镇首次感觉到自己终于在和季然的谈话中爬到了“理”字头上。
“肖帅,你果然很娘……又是珊瑚,又是蒲苇……”季然阴谋再次得逞。
肖镇瞬间从“理”字头上滑落……
“我!带!你!去!见!你!爹!”肖镇把酒杯一放,哼了一声,将毛巾一甩,季然接个正着。
季然好像轻声说了些什么。
肖镇一激灵地回过头来,却没有听见。他看到季然正安静地坐在沙发上。肖镇想问,却没有开口。他又回过身去,走回房间去拿外套,肖镇回想起上次在摩天轮里,季然也好似这样说了些什么,似乎故意不让他听真切,却还是说了,到底是什么,季然,你想说什么,那般小心?
旅途长达6天,途中走走停停,肖镇怕季然吃不消,也不愿在白天开车,终于在另一个滨海之城,肖镇停下了车。
季然并没有要求马上见到季叙风,他和肖镇在海边散了一段步,才好似打起勇气去见他,季然显得格外紧张,他拉住肖镇的手说:“肖镇你知道吗,我其实感谢他取走了我一个肾。”
“什么!”肖镇极度不悦。
“那代表这我们之间不可磨灭的关系,即便他不认我,都无所谓,你知道么……”
肖镇心中叹了叹,他想,当初爱上季然那份特殊的气质大概就是季然那份异于常人的痛苦和不为人知的孤独的照影,肖镇看着月光下的季然,银辉雅致而朦胧地勾勒着季然清秀的轮廓,他此刻才这般肯定,是啊,季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人,甚至是一个舍不得去责备任何人的人,原来凡间真的有天使。
在敲季家大门之前,肖镇忽然拉住季然的手,低低说了声:“等等,季然,我先与他说,我有话问他。”
“肖镇,你不要过激。”季然神色严肃。
“我自然不会。”言罢,肖镇点上了门铃。
来开门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男人,脸上的沟壑显示出他走过的路,他见肖镇虽然身着高雅却非常眼生,一时间并没有打算开启全门的意思。
“请问是季教授吗?”肖镇礼貌地问道。
季叙风闻言以为是学生来了,他“嗯”了一声,“原来是学生吗,稍等……”
待季叙风完全敞开了大门,肖镇冷不防一拳送了上去,季老险些摔倒在地,“你要做什么?”
“要干什么?”肖镇冷笑一声,他仍旧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季然可以,他不行!肖镇正要一脚踢上去的时候,季然忽然呵斥了一声:“肖镇!你干什么!”
“季然,他,他……”肖镇始终不能理解季然为何要维护这个将他弄得遍体鳞伤的人。
“季然?”季叙风一阵惊愕,一阵恐惧,脸色泛起苍白,惊恐的眼神四下打量,看着季然形容肖似当年易云俏,季叙风吓得大气不敢喘。
“季然?”季叙风好不容易站稳了,又问了一遍。
“季然。”季然点了点头。
季叙风见季然对自己似乎并没有敌意,他又将目光放在了肖镇身上,这个人又和自己有什么过节?季然好似瞧出一二,“他是我朋友。”
季叙风刚一个“哦……”字未完,肖镇抓起他的衣领,狠狠问道,“你害了他们母子二十年多年不够,你还要找人取走季然的肾,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你真是猪狗不如,畜生生养!”
“肖镇你住口!”季然连忙上来扯开肖镇钳住季叙风的手。
季叙风闻言也惊讶异常,他只道:“什么?什么?肾源是季然?他们不是说是车祸亡故的男孩吗?”
“你他妈才亡故!”肖镇没好气地一把将季叙风扔在沙发上,“你真不知道?还是装疯卖傻,跟二十五年前一样!”
季叙风脸一阵青一阵白。他忽然变得很沉默。季然和肖镇发觉季叙风一个人住在这大房子里,却没有看到任何家人,墙上也没有哪里有温馨的任何装饰,这一切反映着,季叙风,似乎一直都是单身。
很长一段沉默之后,季叙风忽然道:“季然……你……怎么会是男孩……”季叙风抬起头看着季然,苍老又憔悴,季然忽然对面前的男人心生怜悯,一种无法割断的血亲之情让他一时间忘记过往承受过的一切。
“是啊,我是男孩,母亲死后,我就被云寨送了出来。”季然淡淡地说着,仿佛说着一件与他无关的事。
季叙风变得更加沉默,他望着季然那张消瘦的脸,手伸了一半,却迟迟不敢再继续下去,他深知